жҲ‘зҡ„йқ’жҳҘеңЁиҝҷйҮҢ
еҸ‘зЁҝж—¶й—ҙпјҡ2025-02-17 10:15:00 зј–иҫ‘пјҡжқҺ婧жҖЎ жқҘжәҗпјҡ 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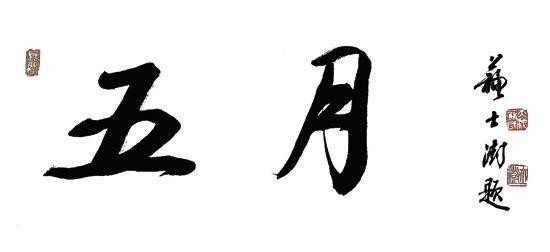

гҖҖгҖҖжӣҫе®Јжқ°/з»ҳ

гҖҖгҖҖзј–иҖ…зҡ„иҜқ
гҖҖгҖҖ2025е№ҙжҳҘиҝҗе·Із»ҸжҺҘиҝ‘е°ҫеЈ°гҖӮеңЁиҝҷеңәи·Ёи¶Ҡеұұжө·зҡ„еӨ§иҝҒеҫҷдёӯпјҢжҜҸдёҖдёӘйқ’е№ҙ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йғҪжҳҜжҳҘиҝҗдәӨе“ҚжӣІдёӯдёҚеҸҜжҲ–зјәзҡ„йҹіз¬ҰгҖӮеңЁжҳҘиҝҗзҡ„дё»жҲҳеңәдёҠпјҢй“Ғи·Ҝйқ’е№ҙ们用жұ—ж°ҙдёҺжҷәж…§пјҢжҺЁеҠЁзқҖдёӯеӣҪй“Ғи·Ҝзҡ„иҝӣжӯҘпјҢи§ҒиҜҒзқҖвҖңжөҒеҠЁзҡ„дёӯеӣҪвҖқеҰӮдҪ•д»Ҙжӣҙеҝ«зҡ„йҖҹеәҰгҖҒжӣҙй«ҳзҡ„ж•ҲзҺҮеҘ”еҗ‘жңӘжқҘгҖӮ他们зҡ„иә«еҪұпјҢжҳҜвҖңеӨ§еӣҪе·ҘзЁӢвҖқдёӯжңҖеҠЁдәәзҡ„йЈҺжҷҜпјҢд№ҹжҳҜвҖңжөҒеҠЁзҡ„дёӯеӣҪвҖқдёӯжңҖжё©жҡ–зҡ„еҠӣйҮҸгҖӮ
гҖҖгҖҖж¬ўиҝҺжҠҠдҪ зҡ„дҪңе“ҒеҸ‘з»ҷвҖңдә”жңҲвҖқпјҲv_zhou@sina.comпјүпјҢдёҺвҖңдә”жңҲвҖқдёҖиө·жҲҗй•ҝгҖӮжү«з ҒеҸҜйҳ…иҜ»гҖҠ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дҪң家жҠҘгҖӢз”өеӯҗзүҲгҖҒ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е®ўжҲ·з«ҜеҲӣдҪңйў‘йҒ“гҖҒ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дҪң家зҪ‘пјҢйӮЈйҮҢжҳҜдёҖзүҮжӣҙеӨ§зҡ„ж–ҮеӯҰиҠұжө·гҖ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жҳҘиҠӮпјҢжҲ‘еңЁжө·жӢ”4702зұізҡ„иҪҰз«ҷеҖје®Ҳ
гҖҖгҖҖе®үжө·е№іпјҲ36еІҒпјүжӢүиҗЁиҪҰеҠЎж®өе®үеӨҡиҪҰз«ҷе®ўиҝҗеҖјзҸӯе‘ҳ
гҖҖгҖҖвҖң1жңҲ28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137дәәпјҢеҲ°иҫҫ140дәәгҖӮвҖқйҷӨеӨ•еҪ“еӨ©пјҢе®үеӨҡз«ҷзҡ„жңҖеҗҺдёҖи¶ҹеҲ—иҪҰZ166ж¬ЎжҷҡзӮ№3еҲҶй’ҹпјҢдәҺ17зӮ№15еҲҶжҠөиҫҫгҖӮдёҠиҪҰж—…е®ў6дәәпјҢдёӢиҪҰ84дәәгҖӮZ166ж¬ЎеҲ—иҪҰй•ҝдёӢиҪҰе’ҢжҲ‘дәӨжҺҘе·ҘдҪңж—¶пјҢиҜҙдәҶдёҖеЈ°вҖңж–°е№ҙеҝ«д№җвҖқгҖӮдёҠиҪҰеүҚпјҢеҲ—иҪҰй•ҝиҝҳжү“и¶Ј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д»ҠеӨ©зҡ„е·ҘдҪңйҮҸжҜ”еүҚеҮ еӨ©еӨ§е“ҹ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йқ’и—Ҹй“Ғи·Ҝиҝӣе…ҘиҘҝи—Ҹзҡ„第дёҖдёӘз«ҷпјҢе®үеӨҡз«ҷжө·жӢ”4702зұіпјҢжҳҜдё–з•ҢдёҠжө·жӢ”жңҖй«ҳзҡ„еҠһзҗҶе®ўиҝҗзҡ„иҪҰз«ҷгҖӮе®үеӨҡз«ҷеұһдәҺвҖңиҝ·дҪ вҖқе°Ҹз«ҷпјҢ300е№іж–№зұізҡ„еҖҷиҪҰе®ӨпјҢеҸӘжңү4жҺ’еә§жӨ…пјҢ72дёӘеә§дҪҚгҖӮж—…е®ўе°‘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дёҖи¶ҹиҪҰиҝӣз«ҷж—¶еҸӘжңүдёүдә”дёӘдәәдёҠдёӢиҪҰгҖӮдҪҶжҜҸеӨ©зҡ„иҝӣз«ҷе®үжЈҖгҖҒеҖҷиҪҰе·Ўи§ҶгҖҒжЈҖзҘЁзҷ»иҪҰиҝҷдәӣе·ҘдҪңпјҢдёҖзӮ№е„ҝд№ҹдёҚиғҪиҗҪдёӢпјҢжҜҸдёҖи¶ҹиҪҰдёҚз®ЎжңүжІЎжңүж—…е®ўпјҢжҲ‘们йғҪеҫ—зӣҜзқҖгҖӮ
гҖҖгҖҖ2013е№ҙпјҢжҲ‘жқҘеҲ°жө·жӢ”3568зұізҡ„жӣІж°ҙз«ҷпјӣ2015е№ҙпјҢжҲ‘и°ғеҲ°жө·жӢ”4513зұізҡ„йӮЈжӣІз«ҷпјӣ2021е№ҙпјҢжҲ‘еҲ°дәҶжө·жӢ”4702зұізҡ„е®үеӨҡз«ҷгҖӮжңүеҗҢдәӢи°ғдҫғжҲ‘пјҢиҜҙжҲ‘жҳҜвҖңжӯҘжӯҘй«ҳеҚҮ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жҷҡдёҠ9зӮ№еӨҡпјҢжҲ‘еңЁз«ҷеҢәйЈҹе Ӯе’ҢйҖҡдҝЎгҖҒз”өеҠЎе·ҘеҢәзҡ„еҗҢдәӢеҗғе®ҢеӣўеңҶйҘӯеҗҺеҗ„иҮӘиҝ”еӣһе®ҝиҲҚгҖӮжҲ–и®ёжҳҜеҗғеҫ—еӨӘйҘұпјҢжҲ‘ж„ҹеҲ°еӨҙеҫҲжІү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зјәж°§дәҶгҖӮжқҘеҲ°еҠһе…¬е®ӨпјҢжҲ‘жҲҙдёҠеҗёж°§з®ЎпјҢжӢ§ејҖ氧气瓶пјҢеҘҪдёҖдјҡе„ҝжүҚзј“иҝҮеҠІжқҘгҖӮ
гҖҖгҖҖе®үеӨҡз«ҷжө·жӢ”й«ҳпјҢж°§ж°”еҗ«йҮҸдҪҺпјҢжһҒжҳ“еј•еҸ‘й«ҳеҺҹеҸҚеә”пјҢжҲ‘们зҡ„еәҠеӨҙгҖҒеҠһе…¬жЎҢйҮҢеЎһж»ЎдәҶзј“и§Јй«ҳеҺҹеҸҚеә”зҡ„иҚҜгҖӮд№ӢеүҚжңүеҗҢдәӢеңЁеё®еҠ©жҗәеёҰеӨ§д»¶иЎҢжқҺзҡ„д№ҳе®ўиө¶иҪҰж—¶пјҢеҸҜиғҪи·‘еҫ—еҝ«дәҶзӮ№пјҢи„ёиүІиӢҚзҷҪгҖҒеҳҙе”ҮеҸ‘зҙ«гҖӮжҲ‘们жҠҠд»–жҠ¬иҝӣеҠһе…¬е®Өеҗёж°§пјҢз…һзҷҪзҡ„и„ёдёҠжүҚжёҗжёҗжңүдәҶиЎҖиүІпјҢеҪ“ж—¶е·®зӮ№е°ұжү“з”өиҜқиҒ”зі»йҖҒеҢ»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вҖң1жңҲ29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37дәәпјҢеҲ°иҫҫ49дәәгҖӮвҖқиҝҷжҳҜд»Ҡе№ҙжҳҘиҠӮе®үеӨҡз«ҷзҡ„д№ҳе®ўж•°йҮҸгҖӮеӨ§е№ҙеҲқдёҖзҡ„第дёҖи¶ҹиҪҰжҳҜд»Һе№ҝе·һејҖеҫҖжӢүиҗЁзҡ„Z265ж¬ЎеҲ—иҪҰпјҢ9зӮ№34еҲҶеҲ°иҫҫе®үеӨҡз«ҷпјҢдёҠиҪҰ14дәәпјҢж— дәәдёӢиҪҰгҖӮеңЁеҖҷиҪҰе®ӨпјҢжҲ‘и·ҹжҜҸдёҖдёӘж—…е®ўйғҪйҒ“дәҶдёҖеЈ°вҖңж–°е№ҙеҘҪвҖқпјҢжӢүдәҶдјҡе„ҝ家常гҖӮдёҖдёӘи—Ҹж—ҸйҳҝеҰҲжӢүзқҖжҲ‘пјҢи·ҹиә«иҫ№дәәиҜҙпјҡвҖңдёҠеӣһжҲ‘еҺ»жӢүиҗЁпјҢе°ұжҳҜиҝҷдёӘиғ–иғ–зҡ„жҲҙзқҖзңјй•ңзҡ„е°Ҹдјҷеӯҗеё®жҲ‘жҸҗзҡ„иЎҢжқҺ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д»ҺеӨ§е№ҙеҲқдёҖејҖе§ӢпјҢдәәжөҒйҮҸйҖҗжёҗеўһеҠ гҖӮвҖң1жңҲ30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38дәәпјҢеҲ°иҫҫ44дәәгҖӮвҖқвҖң1жңҲ31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42дәәпјҢеҲ°иҫҫ70дәәгҖӮвҖқвҖң2жңҲ1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121дәәпјҢеҲ°иҫҫ100дәәгҖӮвҖқвҖң2жңҲ2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144дәәпјҢеҲ°иҫҫ68дәәгҖӮвҖқвҖң2жңҲ3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149дәәпјҢеҲ°иҫҫ84дәәгҖӮвҖқвҖң2жңҲ4ж—ҘпјҢеҸ‘йҖҒ155дәәпјҢеҲ°иҫҫ188дәә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2жңҲ4ж—Ҙе®үеӨҡз«ҷзҡ„ж—…е®ўдёӯпјҢжҲ‘еҚ дәҶдёҖдёӘеҗҚйўқвҖ”вҖ”еҝҷзўҢдәҶдёҖе№ҙпјҢжҲ‘жғіиө¶еңЁжӯЈжңҲеҲқе…«еӯ©еӯҗз”ҹж—Ҙд№ӢеүҚеҲ°е®¶пјҢеҘҪеҘҪйҷӘд»–иҝҮдёӘз”ҹж—ҘгҖӮпјҲеҲҳй’Ҡ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еҮҢжҷЁ4зӮ№зҡ„еҸ«зҸӯжңәпјҢжҳҜжҲ‘дёҺеҚғдёҮж¬ЎеҮҶзӮ№еҮәеҸ‘зҡ„зәҰе®ҡ
гҖҖгҖҖеҫҗиҺәд№ӢпјҲ30еІҒпјүжҲҗйғҪжҲҝе»әе…¬еҜ“ж®өеҸ«зҸӯе‘ҳ
гҖҖгҖҖеӨ§е№ҙеҲқдәҢеҮҢжҷЁ4зӮ№пјҢеҪ“жҲ‘еҜ№еҸёжңәиҜҙвҖңж–°е№ҙеҝ«д№җвҖқ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他们зҡ„еӣһеӨҚдә”иҠұе…«й—ЁпјҡвҖңиғҪжҷҡеҮ еҲҶй’ҹе–ҠжҲ‘еҗ—пјҹвҖқвҖңзқЎйғҪжІЎжңүзқЎйҶ’пјҢи„‘еЈійғҪжҳҜжңЁзҡ„гҖӮвҖқвҖңжё…ж—©е…«жҷЁзҡ„пјҲеӣӣе·қж–№иЁҖпјҡдёҖеӨ§ж—©пјүпјҢиҺ«еӮ¬еҳӣпјҒвҖқвҖҰвҖҰ
гҖҖгҖҖжІЎжі•пјҢжҲ‘еҸӘиғҪзӣјзқҖ他们зҗҶи§ЈгҖӮеӣ дёәжҲ‘жҳҜдёҖеҗҚй“Ғи·ҜеҸ«зҸӯе‘ҳпјҢеңЁи§„е®ҡж—¶й—ҙе–ҠйҶ’иҜҘиө·еәҠзҡ„дәәпјҢзқЈдҝғ他们жҢүж—¶гҖҒеҮҶзӮ№еҮәеҸ‘пјҢе°ұжҳҜжҲ‘зҡ„иҒҢиҙЈгҖӮж—¶й—ҙдёҖеҲ°пјҢдёҖж®өдёҚеёҰж„ҹжғ…зҡ„еЈ°йҹіе°ұдјҡеҮәзҺ°д»–们зҡ„жҲҝй—ҙйҮҢпјҡвҖң2-2-203жҹҗжҹҗеҸёжңәпјҢеҖјд№ҳC****ж¬ЎеҲ—иҪҰпјҢејҖиҪҰж—¶й—ҙ*зӮ№**еҲҶпјҢзҺ°еңЁеҸ«зҸӯпјҢиҜ·жҢүй”®зЎ®и®Ө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жқҘиҝҷдёӘеІ—дҪҚд№ӢеүҚпјҢжҲ‘жҳҜеҲ—иҪҰе‘ҳгҖӮйӮЈж—¶зқЎеңЁзҒ«иҪҰдёҠпјҢеҸ«зҸӯе…Ёйқ жӢҚеәҠжІҝпјҢвҖңз °з °з °вҖқзҡ„еЈ°йҹіи®©жҲ‘дёҚе Әе…¶жү°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жҲ‘жҲҗдёәеҠЁиҪҰеҲ—иҪҰе‘ҳпјҢе·ҘдҪңејәеәҰжӣҙеӨ§пјҢдҪҶиҮіе°‘еәҠй“әдёҚеҶҚиў«жӢҚеҫ—йңҮеӨ©е“ҚгҖӮеҸҜз”ұдәҺдёӢзҸӯж—¶й—ҙиҝҮдәҺйӣҶдёӯпјҢжҺ’йҳҹе…ҘдҪҸе…¬еҜ“жҳҜеёёдәӢпјҢйӮЈж—¶зҡ„жҲ‘еҜ№еҸ«зҸӯе‘ҳд№ҹеҚҒеҲҶеҸҚж„ҹпјҢз”ҡиҮіиҝҳеӣ еҠһзҗҶе…ҘдҪҸеӨӘж…ўе’Ң他们еҗөиҝҮжһ¶гҖӮ
гҖҖгҖҖ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еңЁжҲҗдёәеҸ«зҸӯе‘ҳд№ӢеүҚпјҢжҲ‘еҜ№е…¬еҜ“жҜ«ж— еҘҪж„ҹпјҢз”ҡиҮіеҜ№еҸ«зҸӯе‘ҳе……ж»ЎдәҶеҺҢжҒ¶гҖӮ然иҖҢпјҢ2022е№ҙзҡ„дёҖж¬ЎеІ—дҪҚи°ғж•ҙпјҢи®©жҲ‘жҲҗдәҶиҮӘе·ұжңҖи®ЁеҺҢзҡ„дәәвҖ”вҖ”еҸ«зҸӯе‘ҳгҖӮ
гҖҖгҖҖе°ұеғҸвҖңеҪ“е№ҙе°„еҮәзҡ„еӯҗеј№пјҢеҰӮд»ҠжӯЈдёӯзңүеҝғвҖқгҖӮжӣҫз»ҸжңҖи®ЁеҺҢзҡ„вҖңжү°дәәжё…жўҰвҖқжҲҗдәҶжҲ‘зҡ„ж—Ҙеёёе·ҘдҪңпјҢеҺӢеҠӣжү‘йқўиҖҢжқҘгҖӮжҜҸж¬ЎеҸ«зҸӯжңәе“Қиө·пјҢжҲ‘йғҪдјҡд»Је…Ҙиў«еҸ«йҶ’иҖ…зҡ„и§’иүІпјҢеҝғйҮҢдә”е‘іжқӮйҷҲгҖӮ
гҖҖгҖҖиө·еҲқпјҢжҲ‘жһҒдёҚйҖӮеә”еҮҢжҷЁ2зӮ№еҲ°ж—©дёҠ9зӮ№дёҠеӨңзҸӯпјҢдёүеӣӣзӮ№ж—¶еӣ°еҫ—иҰҒе‘ҪпјҢз”ЁеҶ·ж°ҙжҙ—и„ёгҖҒе–қе’–е•Ўе–қиҢ¶гҖҒиҪ¬еңҲи·әи„ҡзӯүеҗ„з§Қж–№ејҸйғҪз”ЁиҝҮгҖӮиҝҷдёӨе№ҙпјҢжҲ‘еҜ№еҸ«зҸӯе·ҘдҪңжёҗжёҗжңүдәҶжӣҙеӨҡзҡ„дәҶи§ЈгҖӮеүҚиҫҲжқЁиҺ№иҜҙпјҢ1958е№ҙе®қжҲҗзәҝејҖйҖҡж—¶е°ұжңүеҸ«зҸӯе‘ҳдәҶпјҢйӮЈж—¶иҰҒжҢЁдёӘж•Ій—ЁпјҢиҙ№ж—¶иҙ№еҠӣпјӣ20дё–зәӘ90е№ҙд»ЈжңүдәҶйҖҡиҜқеҷЁпјҢеҸҜйҒҮжҖҘдәӢиҝҳеҫ—и·‘иҝҮеҺ»пјӣ2000е№ҙеүҚеҗҺеј•иҝӣеҸ«зҸӯзі»з»ҹпјҢжүҚжңүдәҶеҰӮд»Ҡе·ҘдҪңзҡ„йӣҸеҪўгҖӮ2023е№ҙпјҢжҲ‘и§ҒиҜҒдәҶдәәи„ёиҜҶеҲ«зі»з»ҹзҡ„еј•е…ҘпјҢеҺҹжң¬еҚ•дәәе…ҘдҪҸж—¶й—ҙйңҖ40з§’е·ҰеҸіпјҢзҺ°еңЁ15з§’е°ұиғҪе®ҢжҲҗгҖӮ
гҖҖгҖҖ2025е№ҙжҳҘиҝҗпјҢе№ҝе…ғе…¬еҜ“ж—ҘеқҮеҸ«зҸӯдәәж•°жҝҖеўһиҮіиҝ‘300дәәпјҢе№іеқҮжҜҸ5еҲҶй’ҹе°ұиҰҒе®ҢжҲҗдёҖж¬ЎеҸ«зҸӯж“ҚдҪңгҖӮжҜҸеҪ“еҸ«зҸӯжңәе“Қиө·дёҖж¬ЎпјҢжҲ‘们е°ұиҰҒж ёеҜ№дёҖж¬ЎпјҢзЎ®дҝқеҸ«зҸӯйӣ¶иҜҜе·®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еёёеёёдјҡжғіиө·иҮӘе·ұиҪ¬еІ—еҗҺ第дёҖж¬ЎеҖјеӨңзҸӯж—¶пјҢеҗ¬еҲ°еҸ«зҸӯжңәе“Қиө·ж—¶зҡ„зҙ§еј ж„ҹгҖӮеҸҜеҰӮд»ҠпјҢжҲ‘е·Іжёҗжёҗе–ңж¬ўдёҠдәҶеҸ«зҸӯжңәзҡ„еЈ°йҹігҖӮеӣ дёәе®ғжҜҸе“ҚдёҖж¬ЎпјҢе°ұжңүдёҖжү№дәәеҮҶж—¶еҮәеҸ‘пјҢеҸҲжңүдёҖжү№дәәе№іе®үеҲ°иҫҫгҖӮ
гҖҖгҖҖеҸҳжҲҗиҮӘе·ұи®ЁеҺҢзҡ„дәәпјҢзЎ®е®һжҳҜдёҖз§ҚжҲҗй•ҝгҖӮпјҲеҲҳе…үз…§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жҲ‘зҡ„вҖңйЈҺзҒ«иҪ®вҖқж°ёиҝңеңЁи·ҜдёҠ
гҖҖгҖҖжқҺжҳҹпјҲ29еІҒпјүз„ҰдҪңиҪҰеҠЎж®өз„ҰдҪңиҪҰз«ҷе®ўиҝҗе‘ҳ
гҖҖгҖҖдёӨеә§еҹҺеёӮгҖҒ3дёҮеӨҡжӯҘгҖҒжҳјеӨңдёҚеҒңвҖҰвҖҰеҗ¬еҲ«дәәиҜҙиҝҷе°ұеҸҜд»Ҙз®—вҖңзү№з§Қе…өејҸж—…жёёвҖқдәҶпјҢиҖҢеҜ№жҲ‘жқҘиҜҙпјҢиҝҳиҰҒеҶҚеҠ дёҠдёӨеә§з«ҷжҲҝгҖҒ8дёӘз«ҷеҸ°гҖҒ128и¶ҹж—…е®ўеҲ—иҪҰе’Ңж•°дёҮеҗҚж—…е®ўгҖӮ
гҖҖгҖҖж—©дёҠ6ж—¶пјҢиә«иҫ№дёӨеІҒзҡ„е„ҝеӯҗиҝҳеңЁзҶҹзқЎпјҢжҲ‘ж‘ёй»‘з©ҝеҘҪиЎЈжңҚиҪ»иҪ»е…ідёҠжҲҝй—ЁпјҢејҖе§ӢдәҶиҮӘе·ұвҖңзү№з§Қе…өвҖқзҡ„дёҖеӨ©гҖӮ7ж—¶08еҲҶпјҢеқҗеңЁй«ҳй“ҒдёҠзҡ„жҲ‘д»ҺеҢ…йҮҢжӢҝеҮәж—©йӨҗпјҢд»Һйғ‘е·һеҲ°з„ҰдҪңзҡ„36еҲҶй’ҹиҝҗиЎҢж—¶й—ҙйҮҢпјҢжҲ‘еҸҜд»ҘзӣёеҜ№д»Һе®№ең°еҗғе®ҢгҖӮ7ж—¶42еҲҶпјҢеҲ—иҪҰжҠөиҫҫз„ҰдҪңиҪҰз«ҷпјҢжҲ‘иҝ…йҖҹжҚўеҘҪеҲ¶жңҚпјҢз©ҝжҲҙеҘҪи®ҫеӨҮеҗҺдҫҝжҠ•е…Ҙе·ҘдҪңеҪ“дёӯгҖӮз„ҰдҪңиҪҰз«ҷдёҚз®—еӨ§пјҢдҪҶжҳҜжҜҸеӨ©йқўеҜ№зҡ„е·ҘдҪңдёҖзӮ№д№ҹдёҚе°‘пјҡжЈҖжҹҘиҪҰз«ҷи®ҫеӨҮгҖҒеј•еҜјж—…е®ўд№ҳиҪҰгҖҒжҺҘеҸ—ж—…е®ўе’ЁиҜўгҖҒеё®жү¶йҮҚзӮ№ж—…е®ўгҖҒеӨ„зҗҶзӘҒеҸ‘зҠ¶еҶөвҖҰвҖҰеҲҡиҝҮ12ж—¶пјҢжҲ‘е°ұе·Із»Ҹиө°дәҶдёӨдёҮеӨҡжӯҘгҖӮеҗҢдәӢ们жҖ»иҜҙпјҢжқҺжҳҹеҜ№еҲ«зҡ„йғҪжІЎд»Җд№ҲиҰҒжұӮпјҢдҪҶжҳҜйһӢеӯҗдёҖе®ҡеҫ—жҳҜжңҖиҲ’жңҚзҡ„гҖӮеҗҢдәӢ们йғҪиҜҙжҲ‘еғҸиё©зқҖвҖңйЈҺзҒ«иҪ®вҖқзҡ„е°Ҹе“Әеҗ’пјҢжҲ‘д№ҹе–ңж¬ўиҝҷдёӘз§°е‘јгҖӮеӨҡиө°дёҖжӯҘпјҢд№ҹи®ёе°ұиғҪеӨҡеё®еҠ©дёҖеҗҚж—…е®ўйЎәеҲ©еҮәиЎҢпјҢеҸӘиҰҒж—…е®ўйңҖиҰҒпјҢжҲ‘зҡ„вҖңйЈҺзҒ«иҪ®вҖқе°ұж°ёиҝңеңЁи·ҜдёҠгҖӮ
гҖҖгҖҖ13ж—¶пјҢжҲ‘еқҗдәҶдёӢжқҘеҮҶеӨҮз”ЁйӨҗпјҢеҲҡеҗғжІЎеҮ еҸЈпјҢеҜ№и®Іжңәе°ұеҸҲе“ҚдәҶиө·жқҘпјҢеҖҷиҪҰе®ӨеҶ…дёҖеҗҚе„ҝз«Ҙй«ҳзғ§жғҠеҺҘпјҢжҖҘйңҖеё®еҠ©гҖӮеғҸиҝҷж ·зҡ„зӘҒеҸ‘дәӢ件пјҢжҲ‘жҜҸеӨ©йғҪдјҡйҒҮеҲ°еҫҲеӨҡпјҢеҜ№жҲ‘жқҘиҜҙжҳҜиҖғйӘҢд№ҹжҳҜжҲҗй•ҝ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й«ҳй“ҒдёҠйӮЈйЎҝж—©йӨҗжҲ‘дёҖиҲ¬йғҪдјҡз»ҷиҮӘе·ұе®үжҺ’дё°зӣӣдёҖдәӣпјҢи·ҜдёҠеӨҡеҗғзӮ№гҖӮ
гҖҖгҖҖвҖңеҰҲеҰҲжҳҺеӨ©е°ұеӣһ家е•ҰпјҢеңЁе®¶иҰҒд№–д№–еҗ¬иҜқпјҢжҷҡе®үе“ҰпјҒвҖқ21ж—¶и®ёпјҢжҲ‘жҢӮж–ӯдәҶе’Ң家дәәзҡ„и§Ҷйў‘з”өиҜқпјҢз©ҝдёҠеҺҡеҺҡзҡ„еӨ§иЎЈеүҚеҫҖз«ҷеҸ°гҖӮз„ҰдҪңиҪҰз«ҷжҳҜдёҖеә§йӣҶй«ҳй“ҒгҖҒжҷ®йҖҹгҖҒеҹҺйҷ…дәҺдёҖдҪ“зҡ„е®ўиҝҗиҪҰз«ҷпјҢзңјдёӢжӯЈеҖјиҝ”зЁӢе®ўжөҒй«ҳеі°жңҹпјҢж—…е®ўз»„з»Үе®№дёҚеҫ—еҚҠзӮ№й©¬иҷҺгҖӮжңүдәӣж—…е®ўдјҡеӣ дёәеҖҷиҪҰж—¶зқЎзқҖиҖҢй”ҷиҝҮеҲ—иҪҰпјҢйңҖиҰҒжҲ‘们еҶҚеӨҡжҸҗйҶ’еҮ еҸҘгҖӮж—¶й’ҹе·Із»ҸжҢҮеҗ‘йӣ¶зӮ№пјҢжҲ‘дҫқ然еңЁеҖҷиҪҰе®ӨгҖҒз«ҷеҸ°й—ҙжқҘеӣһз©ҝжўӯпјҢжҲ‘зҡ„еҫ®дҝЎиҝҗеҠЁжӯҘж•°д№ҹеңЁеӨ§еӨҡж•°дәәзҶҹзқЎзҡ„ж—¶еҖҷйҮҚж–°вҖңйңёжҰң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ж—©дёҠ5ж—¶37еҲҶпјҢйҖҒиө°K589ж¬ЎеҲ—иҪҰзҡ„ж—…е®ўеҗҺпјҢжҲ‘зүҮеҲ»дёҚеҒңд»ҺеҢ—з«ҷжҲҝиө¶еҫҖеҚ—з«ҷжҲҝпјҢиҝҺжҺҘеҪ“еӨ©з¬¬дёҖжү№д№ҳеқҗй«ҳй“Ғзҡ„ж—…е®ўпјҢG1585ж¬ЎеҲ—иҪҰе°ҶдәҺеҚҠе°Ҹж—¶еҗҺд»Һз„ҰдҪңиҪҰз«ҷе§ӢеҸ‘пјҢеүҚеҫҖйҰ–йғҪеҢ—дә¬гҖӮжҳҘиҝҗиҝҳеңЁз»§з»ӯпјҢдҪңдёәй“Ғи·ҜдәәпјҢи®©жӣҙеӨҡдәәиғҪеӨҹйЎәйЎәеҪ“еҪ“еӣһ家иҝҮе№ҙпјҢеҶҚе№іе№іе®үе®үиҝ”зЁӢпјҢе°ұжҳҜжҲ‘зҡ„иҙЈд»»гҖӮпјҲйӮұжҷ¶ еј еҚ“зҫӨ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иҖҒ乡们зҡ„е№ёзҰҸе°ұжҳҜжҲ‘еҘ”еҝҷзҡ„ж„Ҹд№ү
гҖҖгҖҖе‘ЁеӯҰе…ҡпјҲ29еІҒпјүжҳҶжҳҺе®ўиҝҗж®өеҲ—иҪҰе‘ҳ
гҖҖгҖҖеңЁжҲ‘зҡ„11дёӘжҳҘиҝҗйҮҢпјҢжҲ‘дәІеҺҶдәҶдә‘еҚ—д»Һжҷ®йҖҹеҲ—иҪҰж—¶д»Јиө°иҝӣй«ҳй“Ғж—¶д»ЈпјҢеҖјд№ҳдә‘еІӯеҠЁиҪҰејҖеҲ°дәҶзҫҺдёҪзҡ„иҘҝеҸҢзүҲзәіпјҢеҸҲејҖеҲ°дәҶйӣӘеҹҹзҡ„йҰҷж јйҮҢжӢүпјҢдҪ“дјҡзқҖж—…е®ўд»ҺвҖңиө°еҫ—дәҶвҖқеҲ°вҖңиө°еҫ—еҘҪвҖқзҡ„е®һеңЁиҪ¬еҸҳпјҢж„ҹеҸ—зқҖй«ҳй“ҒдҫҝжҚ·иҲ’йҖӮ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ж„ҹеҸ—зқҖж…ўзҒ«иҪҰзҡ„и„үи„үжё©жғ…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ж—ҘеёёеҖјд№ҳжҳҶжҳҺиҮійҰҷж јйҮҢжӢүзҡ„вҖңе…ұйқ’еӣўеҸ·вҖқеҲ—иҪҰд»ҘеҸҠдёӯиҖҒй“Ғи·Ҝж–№еҗ‘зҡ„еҲ—иҪҰгҖӮдј‘жҒҜж—¶й—ҙпјҢжҲ‘дјҡе’Ңе°Ҹдјҷдјҙ们дёҖиө·пјҢеҝ—ж„ҝеҖјд№ҳвҖңе…ұйқ’еӣўеҸ·вҖқе…¬зӣҠжҖ§ж…ўзҒ«иҪҰгҖӮй“Ғи·ҜжІҝзәҝйӮЈдәӣжҢ‘зқҖ蔬иҸңзҡ„иҖҒд№ЎпјҢејӮең°дёҠеӯҰ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иҝҳжңүж—Ҙеёёиө°дәІи®ҝеҸӢгҖҒеӨ–еҮәеҠЎе·ҘгҖҒиҝӣеҹҺе°ұеҢ»зҡ„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еҗҢиғһпјҢйғҪдјҡеқҗж…ўзҒ«иҪҰеҮәиЎҢпјҢеҖјд№ҳвҖңе…ұйқ’еӣўеҸ·вҖқзҡ„еҝ—ж„ҝиҖ…йғҪжҳҜй«ҳй“Ғеҗ„жқЎзәҝдёҠзҡ„еӣўе‘ҳйқ’е№ҙгҖӮеңЁзү№ж®Ҡж—¶жңҹпјҢдјҡејҖиЎҢвҖңе…ұйқ’еӣўеҸ·вҖқдёӯй«ҳиҖғдё“еҲ—е’ҢеҠЎе·Ҙдё“еҲ—пјҢй’ҲеҜ№жҖ§жңҚеҠЎеӨҮиҖғеӯҰз”ҹе’ҢеҠЎе·Ҙдәәе‘ҳгҖӮд»Ҡе№ҙпјҢд№ҹжҳҜжҲ‘еҝ—ж„ҝеҖјд№ҳзҡ„第10е№ҙгҖӮ
гҖҖгҖҖ7ж—¶18еҲҶпјҢ5652ж¬ЎвҖңе…ұйқ’еӣўеҸ·вҖқе…¬зӣҠжҖ§ж…ўзҒ«иҪҰеңЁжҷЁе…үдёӯ驶еҮәжҳҶжҳҺз«ҷгҖӮеҲ—иҪҰйҖ”з»Ҹзҡ„з…§зҰҸй“әгҖҒеҗҙе®ҳз”°гҖҒ马йҫҷзӯүз«ҷпјҢиҸңеҶң们иҰҒеүҚеҫҖжӣІйқ–зҒ«иҪҰз«ҷж—Ғзҡ„е•ҶдёҡиЎ—иҸңеёӮеңәгҖӮиҖҒ乡们用дёҖж №жүҒжӢ…пјҢжҢ‘дёӨдёӘиҸңзӯҗпјҢдёҖзӯҗиҸңеӨ§жҰӮжңү20еӨҡе…¬ж–ӨгҖӮ
гҖҖгҖҖеҲ°з«ҷеүҚпјҢжҲ‘们дјҡжҸҗеүҚз–ҸйҖҡеҘҪиҝҮйҒ“пјҢз»„з»Ү旅客们еҲ°иҪҰй—ЁеҸЈзӯүеҖҷпјҢж…ўзҒ«иҪҰз»ҸеҒңзҡ„еҹәжң¬йғҪжҳҜдҪҺз«ҷеҸ°пјҢиҖҒдәәеӯ©еӯҗ们дёҠдёӢиҪҰдёҚж–№дҫҝпјҢе°Өе…¶иҰҒжіЁж„Ҹе®үе…ЁгҖӮ
гҖҖгҖҖеҒңиҪҰеҲ°з«ҷпјҢжҲ‘们йғҪдјҡжӢӣе‘јиҖҒ乡们д»ҺиҮӘе·ұжүҖеңЁиҪҰеҺўзҡ„иҪҰй—ЁдёҠиҪҰпјҢжң¬еҠЎзҸӯз»„иҒҢе·ҘеӨ§йғЁеҲҶйғҪжҳҜиҖҒеёҲеӮ…дәҶпјҢиҝҷдәӣдҪ“еҠӣжҙ»жҲ‘们е№ҙиҪ»дәәжқҘе°ұиЎҢгҖӮ
гҖҖгҖҖз«ҷеҸ°дёҠпјҢиҖҒ乡们жӯҘеұҘеҢҶеҢҶгҖҒ笑ж„ҸзӣҲзӣҲпјҢжӢ…еӯҗйҮҢжҳҜжІүз”ёз”ёзҡ„е№ёзҰҸпјҢиө·ж—©иҙӘй»‘д№ҹд»ҺдёҚи§үеҫ—иҫӣиӢҰ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зҡ„е№ёзҰҸпјҢе°ұеңЁиҖҒ乡们зҡ„е№ёзҰҸд№ӢдёӯпјҢиҖҢе®үе…ЁжүҚжҳҜи®©иҝҷе№ёзҰҸй•ҝй•ҝд№…д№…зҡ„еүҚжҸҗе’ҢеҹәзЎҖгҖӮдёәдҝқйҡңж—…е®ўдёҠдёӢиҪҰе®үе…ЁпјҢжҲ‘们йғҪдјҡдёӨдёӨжҗӯжЎЈпјҢдёҖдәәеңЁиҪҰдёҠпјҢдёҖдәәеңЁиҪҰдёӢпјҢжҠұеӯ©еӯҗгҖҒжҗ¬иЎҢжқҺгҖҒжҠ¬з®©зӯҗпјҢж—…е®ўдёҠдёӢиҪҰж—¶жҲ‘们еҶҚжү¶дёҖжҠҠгҖҒжӢүдёҖдёӢгҖӮ
гҖҖгҖҖиҪҰеҺўйҮҢпјҢдёҠдәҶе№ҙзәӘзҡ„иҸңеҶңеҜ№жүӢжңәж”Ҝд»ҳдёҚзҶҹжӮүпјҢжҲ‘е°ұжҢЁдёӘеё®еӨ§е®¶жҠҠеҫ®дҝЎж”¶ж¬ҫдәҢз»ҙз Ғи®ҫзҪ®жҲҗжүӢжңәжЎҢйқўпјҢеҶҚи®ҫзҪ®еҘҪ收ж¬ҫеҲ°иҙҰжҸҗзӨәгҖӮиҝӣеҮәз«ҷж—¶иҰҒеҲ·иә«д»ҪиҜҒпјҢжҲ‘е°ұеҮҶеӨҮеҘҪеёҰз»іеңҲзҡ„еҚЎеҘ—пјҢиҝҷж ·е°ұдёҚе®№жҳ“еј„дёўгҖӮиҝҳжңүиҖҒ乡们жҖ»иҜҙзҡ„пјҢжүӢжңәиҖҒжҸҗзӨәеҶ…еӯҳдёҚеӨҹпјҢжҲ–иҖ…еҸҲиҜҜи§Ұйқҷйҹій”®гҖҒдёҚе“Қй“ғзӯүй—®йўҳпјҢйғҪжҳҜжҲ‘иҮӘе·ұ家зҡ„иҖҒдәәеёёдјҡйҒҮеҲ°зҡ„дәӢпјҢзңӢзқҖеқҗиҪҰзҡ„иҖҒ乡们пјҢжҲ‘д№ҹжҖ»жғіеҲ°иҮӘе·ұзҡ„家йҮҢдәә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жҳҜвҖңе…ұйқ’еӣўеҸ·вҖқжҠҠжҲ‘们еҸҳжҲҗдәҶдёҖ家дәәгҖӮ
гҖҖгҖҖиҝҷж¬ЎпјҢжҲ‘们иҝҳжҸҗеүҚжҺ’з»ғдәҶиҠӮзӣ®пјҢеёҰдёҠжүӢйј“е’Ңйҹіе“ҚпјҢе’Ң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еҗҢиғһ们ејҖеұ•дәҶдёҖеңәеұұжӯҢе’ҢвҖңжү“и·івҖқгҖӮеңЁеӨ§е®¶зҡ„笑声жҺҢеЈ°дёӯпјҢеңЁиҖҒ乡们зҡ„ејҜејҜзңүзңје’ҢдёҠжү¬еҳҙи§’йҮҢпјҢжҲ‘ж„ҹеҸ—еҲ°дәҶе…·иұЎеҢ–зҡ„е№ёзҰҸпјҢиҝҷд№ҹжҳҜжҜҸдёҖдёӘжҳҘиҝҗжҲ‘ж„ҝж„Ҹдёәд№ӢеҘ”еҝҷзҡ„ж„Ҹд№үгҖӮпјҲжқҺиӢ‘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йқ’жҳҘи·ғеҠЁеңЁвҖңз»ҝе·ЁдәәвҖқзҡ„и„үжҗҸйҮҢ
гҖҖгҖҖеҖӘж¶өзҗӘпјҲ24еІҒпјүеҚ—жҳҢе®ўиҝҗж®өеҲ—иҪҰеҖјзҸӯе‘ҳ
гҖҖгҖҖдҪ жҳҜеҗҰи§ҒиҝҮпјҢдёҖеҲ—вҖңз»ҝе·ЁдәәвҖқеҠЁеҚ§йЈһй©°иҖҢиҝҮпјҹиҝҷиҫҶиҝҗиЎҢеңЁдә¬д№қзәҝдёҠзҡ„еҠЁеҠӣйӣҶдёӯеҠЁиҪҰз»„пјҢдёҚд»…жҳҜиҝһжҺҘйқ©е‘ҪеңЈең°дә•еҶҲеұұдёҺйҰ–йғҪеҢ—дә¬дёӨең°зҡ„зәўиүІзәҪеёҰпјҢжӣҙжҳҜж— ж•°йқ©е‘ҪзІҫзҘһзҡ„延з»ӯпјҢж»ЎиҪҪзқҖи¶…иҝҮеҚғдәәзҡ„еёҢжңӣдёҺжўҰжғіпјҢдёҖи·ҜйЈһй©°йҖҗжўҰ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пјҢжңүе№ёжҲҗдёәиҝҷи¶ҹCR200JеһӢеӨҚе…ҙеҸ·вҖңдә•еҶҲеұұеҸ·вҖқеҲ—иҪҰдёҠзҡ„дёҖе‘ҳпјҢеҖјд№ҳзқҖD134ж¬ЎеҲ—иҪҰгҖӮ20ж—¶58еҲҶпјҢжҲ‘дёҺд№ҳеҠЎзҸӯз»„еңЁеҚ—жҳҢиҘҝз«ҷеҮҶж—¶жҺҘзҸӯгҖӮйҡҸзқҖеҲ—иҪҰзј“зј“еҗҜеҠЁпјҢз«ҷеҸ°зҡ„еӨңе…үйҖҗжёҗиҝңеҺ»пјҢжҲ‘зҙ§еј иҖҢжңүеәҸзҡ„е·ҘдҪңд№ҹйҡҸд№ӢжӢүејҖеәҸ幕гҖӮ
гҖҖгҖҖ9еҸ·гҖҒ10еҸ·иҪҰеҺўжҳҜжҲ‘зҡ„дё»жҲҳеңәгҖӮдёҖиҠӮеҸӘжңү25.5зұізҡ„иҪҰеҺўпјҢеҪ“дёҠеә§зҺҮиҫҫеҲ°100%ж—¶пјҢжҲ‘иЎҢиө°дёҖи¶ҹиҮіе°‘и¶…иҝҮ12000жӯҘгҖӮд»ҺеҲ—иҪҰеҗҜеҠЁзҡ„йӮЈдёҖеҲ»иө·пјҢзӣҙиҮіеӨңй—ҙ24ж—¶пјҢжҲ‘еҮ д№ҺдёҚеҒңжӯҮең°еңЁиҪҰеҺўеҶ…з©ҝжўӯпјҡе®һеҗҚеҲ¶ж ёйӘҢгҖҒеҲ°з«ҷжҸҗзӨәжҸҗйҶ’гҖҒдёәж—…е®ўзӯ”з–‘и§Јжғ‘гҖҒз…§йЎҫйҮҚзӮ№ж—…е®ўвҖҰвҖҰ
гҖҖгҖҖдёәдәҶзЎ®дҝқеӨңй—ҙе’Ңж¬Ўж—Ҙжё…жҷЁж—…е®ўзҡ„жҙ—жјұйҖҡз•…пјҢжҲ‘们дјҡд»Һ23ж—¶иө·ејҖе§ӢеҜ№еҚ«з”ҹй—ҙгҖҒжҙ—и„ёй—ҙзӯүиҝӣиЎҢйҮҚзӮ№жё…жҙҒгҖӮжңүж—¶пјҢдёҖдәӣж—…е®ўдјҡиў«жҲ‘们вҖңжҙ—еҲ·еҲ·вҖқе’Ңж°ҙжЎ¶зҡ„зў°ж’һеЈ°жүҖеҗёеј•пјҢжҠ•жқҘеҘҪеҘҮзҡ„зӣ®е…үпјӣдҪҶжӣҙеӨҡ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他们еҸӘжҳҜжІүжөёеңЁж•ҙжҙҒиҲ’йҖӮзҡ„зҺҜеўғдёӯе®үеҝғдј‘жҶ©гҖӮ
гҖҖгҖҖж·ұеӨңж—¶еҲҶпјҢж—…е®ўе·Іе®ү然е…ҘжўҰгҖӮжҲ‘еҲҷеҢ–иә«дёәеӨңзҡ„е®ҲжңӣиҖ…пјҢеңЁиҪҰеҺўиҫ№еҮійқҷеқҗеҖје®ҲгҖӮй•ҝжңҹзҡ„е·ҘдҪңдҪҝ然пјҢжҲ‘з»ғе°ұдәҶвҖңзҒ«зңјйҮ‘зқӣвҖқе’ҢвҖңзҒөж•Ҹзҡ„йј»еӯҗвҖқпјҢеҚіж•Ҹй”җзҡ„и§ӮеҜҹеҠӣе’ҢиӯҰи§үжҖ§пјҢд»Ҙйў„йҳІж—…е®ўеҗёзғҹзӯүжҪңеңЁзҡ„е®үе…ЁйҡҗжӮЈгҖӮ
гҖҖгҖҖжё…жҷЁ5ж—¶30еҲҶпјҢйҡҸзқҖеҚ§й“әиҪҰеҺўзӘ—еёҳзј“зј“жӢүејҖпјҢзІүи“қдәӨз»Үзҡ„ж—ҘеҮәжҷҜиұЎжҳ е…ҘзңјеёҳпјҢеӨ©йҷ…жёҗжёҗз»Ҫж”ҫеҮәжё©жҹ”зҡ„жҷЁе…үгҖӮиҖҢжҲ‘пјҢеҸҲиҝҺжқҘдәҶж–°дёҖеӨ©зҡ„еҝҷзўҢдёҺжҢ‘жҲҳгҖӮеҲ—иҪҰ缓缓驶е…Ҙз«ҷеҸ°пјҢзӣ®йҖҒзқҖ旅客们еёҰзқҖж»Ўж„Ҹзҡ„笑容зҰ»еҺ»пјҢ他们зҡ„иғҢеҪұеңЁжҷЁе…үдёӯжёҗжёҗжӢүй•ҝпјҢжҲ‘зҡ„еҝғдёӯдҫҝж¶ҢеҠЁиө·дёҖиӮЎйҡҫд»ҘиЁҖе–»зҡ„иҮӘиұӘдёҺж»Ўи¶ігҖӮеӣ дёәжҲ‘зҹҘйҒ“пјҢиҝҷд»Ҫе·ҘдҪңиөӢдәҲжҲ‘зҡ„пјҢиҝңдёҚеҸӘжҳҜдёәж—…е®ўжҸҗдҫӣе‘ЁеҲ°зҡ„жңҚеҠЎйӮЈд№Ҳз®ҖеҚ•гҖӮе®ғжӣҙжҳҜдёҖз§ҚзІҫзҘһзҡ„дј йҖ’пјҢдёҖз§ҚеҠӣйҮҸзҡ„еҮқиҒҡгҖӮеңЁиҝҷж— е°Ҫзҡ„й“ҒиҪЁдёҠпјҢжҲ‘з”Ёеҝғд№ҰеҶҷзқҖиҮӘе·ұзҡ„йқ’жҳҘж•…дәӢпјҢе°Ҷжё©жҡ–дёҺе…іжҖҖж’ӯж’’еңЁжҜҸдёҖеӨ„и§’иҗҪгҖӮиҖҢйӮЈдәӣжёҗиЎҢжёҗиҝңзҡ„иғҢеҪұпјҢдҫҝжҳҜеҜ№жҲ‘е·ҘдҪңжңҖеӨ§зҡ„иӮҜе®ҡгҖӮ
гҖҖгҖҖеҲ—иҪҰеҲ°з«ҷдәҶпјҢжҲ‘зҡ„йқ’жҳҘеҚҙ并жңӘз”»дёҠеҸҘеҸ·пјҢдҫқж—§и·ғеҠЁеңЁиҝҷвҖңз»ҝе·ЁдәәвҖқзҡ„и„үжҗҸдёӯгҖӮпјҲжқЁй“ӯйёЈ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дёҮеҗЁе·ЁиҪ®дёҠйҖҗжўҰжҳҹиҫ°еӨ§жө·
гҖҖгҖҖеҫҗж–Үй№ҸпјҲ28еІҒпјүжө·еҸЈжңәиҫҶиҪ®жёЎж®өдёүз®ЎиҪ®
гҖҖгҖҖз–Ҹж·Ўзҡ„дә‘пјҢж— еһ зҡ„жө·пјҢ咸涩зҡ„йЈҺвҖҰвҖҰеҲқзҷ»зІӨжө·й“Ғи·ҜиҲ№иҲ¶пјҢзңјеүҚзҡ„дёҖеҲҮйҷҢз”ҹиҖҢйңҮж’јгҖӮе·ЁеӨ§зҡ„иҲ№дҪ“пјҢеӨҚжқӮзҡ„жңәжў°иЈ…зҪ®пјҢиҝҳжңүжү‘йқўиҖҢжқҘзҡ„ж»ҡж»ҡзғӯжөӘвҖҰвҖҰ
гҖҖгҖҖ6е№ҙеүҚпјҢжҲ‘иө°еҮәеӨ§еӯҰпјҢиёҸдёҠз”Іжқҝзҡ„еҲ№йӮЈпјҢжўҰжғіз…§иҝӣзҺ°е®һгҖӮиҲ№иҲ¶жңәиҲұдҪҚдәҺж°ҙзәҝд»ҘдёӢ5.5зұіпјҢеҰӮеҗҢдёҮеҗЁе·ЁиҪ®зҡ„вҖңеҝғи„ҸвҖқпјҢж—¶еҲ»дёәиҲ№иҲ¶жҸҗдҫӣжәҗжәҗдёҚж–ӯзҡ„еҠЁеҠӣпјҢжҳҜдҝқйҡңиҲӘиЎҢе®үе…Ёзҡ„е…ій”®еҢәеҹҹгҖӮд»Һз”ІжқҝдёӢеҲ°жңәиҲұпјҢиҰҒиө°4еұӮжҘјжўҜгҖҒ50дёӘеҸ°йҳ¶пјҢеһӮзӣҙй«ҳеәҰзәҰ12зұіпјҢеқЎеәҰиҝ‘55еәҰгҖӮдҪңдёҡдәәе‘ҳдёҠдёӢжҘјжўҜйғҪиҰҒжү¶зҙ§жҠҠжүӢпјҢдёҖдёӘзҸӯдёӢжқҘпјҢиҮіе°‘иҰҒеңЁжңәиҲұдёҺз”Іжқҝд№Ӣй—ҙеҫҖиҝ”10и¶ҹпјҢзӣёеҪ“дәҺзҲ¬80еұӮжҘјгҖӮ
гҖҖгҖҖдёүз®ЎиҪ®зҡ„е·ҘдҪңзҗҗзўҺиҖҢз№ҒеӨҡгҖӮжҜҸеӨ©пјҢжҲ‘йғҪиҰҒдёҘж јжҢүз…§жөҒзЁӢе·ЎжЈҖеҲҶз®Ўзҡ„и®ҫеӨҮпјҢд»Һж¶ҲйҳІж°ҙжіөеҲ°ж•‘з”ҹиүҮжңәпјҢд»ҺиӢұзү№зҒөзі»з»ҹеҲ°з”Іжқҝжңәжў°вҖҰвҖҰжҜҸдёҖдёӘйғЁд»¶йғҪиҰҒд»”з»ҶжЈҖжҹҘпјҢеҗ¬е®ғ们иҝҗиЎҢзҡ„еЈ°йҹіжҳҜеҗҰжӯЈеёёпјҢзңӢеҗ„йЎ№еҸӮж•°жҳҜеҗҰз¬ҰеҗҲ规е®ҡгҖӮ
гҖҖгҖҖе·ҘдҪңж—¶пјҢж•ҙдёӘзҸӯз»„24е°Ҹж—¶йғҪеңЁиҲ№дёҠгҖӮеҗ„з§Қи®ҫеӨҮеҗҢж—¶иҝҗиҪ¬пјҢжңәиҲұеҶ…жңәеҷЁиҪ°йёЈпјҢеЈ°йҹіеңЁ70еҲ°80еҲҶиҙқй—ҙпјҢдё»жңәиҲұжӣҙжҳҜй«ҳиҫҫ110еҲҶиҙқгҖӮ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зҺҜеўғдёӢпјҢжҲ‘е’ҢеҗҢдәӢйқўеҜ№йқўи®ІиҜқд№ҹеҫҲйҡҫеҗ¬жё…пјҢзӣёдә’дәӨжөҒеҸӘиғҪз”ЁжүӢжҜ”з”»гҖӮз”ұдәҺз©әй—ҙе°Ғй—ӯпјҢеҠ д№Ӣи®ҫеӨҮжҳјеӨңиҝҗиҪ¬ж•ЈеҸ‘зҡ„зғӯйҮҸпјҢжңәиҲұеҶ…еёёе№ҙжҳҜ40иҮі50ж‘„ж°ҸеәҰзҡ„й«ҳжё©пјҢеҮ еҲҶй’ҹдёӢжқҘпјҢе…Ёиә«еҫҲеҝ«ж№ҝйҖҸ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зҡ„иҖҒ家еңЁеҗүжһ—еӣӣе№іпјҢи·қжө·еҸЈ3400еӨҡе…¬йҮҢгҖӮе·ҘдҪңд»ҘеҗҺпјҢиҝңзҰ»е®¶дәәзҡ„йҷӘдјҙпјҢеӯӨзӢ¬ж„ҹж—¶еёёж¶ҢдёҠеҝғеӨҙ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иҠӮеҒҮж—ҘпјҢжңӣзқҖзӘ—еӨ–иҢ«иҢ«зҡ„еӨ§жө·пјҢеҗ¬еҲ°е®ўиҲұйҮҢ旅客们зҡ„欢声笑иҜӯпјҢжҖқеҝөд№Ӣжғ…ж„ҲеҸ‘жө“зғҲгҖӮдҪҶеҘҪеңЁиҲ№дёҠжңүдёҖзҫӨеҝ—еҗҢйҒ“еҗҲзҡ„дјҷдјҙгҖӮжҲ‘们дёҖиө·е·ҘдҪңпјҢдёҖиө·з”ҹжҙ»пјҢдј‘жҒҜж—¶пјҢжңүдәәжӢҝеҮәеҗүд»–пјҢиҪ»иҪ»еј№е”ұйқ’жҳҘзҡ„ж—ӢеҫӢпјӣжңүдәәеұ•зӨәеҺЁиүәпјҢеҒҡеҮәдёҖйҒ“йҒ“зҫҺе‘ідҪіиӮҙпјҢз»ҷе№іж·Ўзҡ„ж—ҘеӯҗжҚўдёҖз§Қе‘ійҒ“пјӣйҒҮеҲ°з”ҹж—ҘпјҢжҲ‘们дјҡдёҫеҠһдёҖеңәзү№еҲ«зҡ„жҙҫеҜ№вҖҰвҖҰж‘Үжӣізҡ„зғӣе…үжҳ з…§зқҖеӨ§е®¶ж»ЎжҳҜжұ—ж°ҙеҚҙеҸҲжҙӢжәўзқҖ笑容зҡ„и„ёеәһпјҢиҝҷдёҖеҲ»пјҢжүҖжңүзҡ„иҫӣиӢҰе’Ңз–Іжғ«йғҪиў«жҠӣеҲ°д№қйң„дә‘еӨ–гҖӮ
гҖҖгҖҖ6е№ҙж—¶й—ҙпјҢжҲ‘зҶҹз»ғжҺҢжҸЎдәҶеҗ„з§Қи®ҫеӨҮзҡ„ж“ҚдҪңе’Ңз»ҙдҝ®пјҢеӯҰдјҡеңЁеӨҚжқӮ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еҶ·йқҷеҲҶжһҗй—®йўҳгҖҒи§ЈеҶій—®йўҳгҖӮдҪңдёәиҲ№иҲ¶иҝҗиЎҢзҡ„е…ій”®дҝқйҡңдәәе‘ҳд№ӢдёҖпјҢжҲ‘зҡ„жҜҸдёҖдёӘеҶізӯ–гҖҒжҜҸдёҖж¬Ўж“ҚдҪңпјҢйғҪе…ізі»еҲ°ж—…е®ўзҡ„е®үе…ЁгҖӮиҝҷд»ҪиҙЈд»»пјҢи®©жҲ‘дёҚж–ӯеҠӘеҠӣжҸҗеҚҮиҮӘе·ұпјҢд»ҺдёҚжҮҲжҖ гҖӮжҲ‘жғіпјҢиҝҷе°ұжҳҜйқ’жҳҘзҡ„еә•иүІеҗ§вҖ”вҖ”дёҚз•Ҹиү°йҡҫпјҢеӢҮеҫҖзӣҙеүҚпјҢз”Ёжұ—ж°ҙе’Ңжҷәж…§д№ҰеҶҷ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зІҫеҪ©зҜҮз« гҖӮ(马鑫 ж•ҙзҗҶ)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жңәиҪҰйҡҶйҡҶзј–з»ҮйҡҫеҝҳзҜҮз«
гҖҖгҖҖи°·йҮ‘йҡҶпјҲ26еІҒпјүйғ‘е·һжңәеҠЎж®өжңәиҪҰй’іе·Ҙ
гҖҖгҖҖж—¶й—ҙиҝҮеҫ—зңҹеҝ«пјҢиҪ¬зңјй—ҙпјҢжҲ‘еңЁеҶ…зҮғжңәиҪҰй’іе·ҘеІ—дҪҚдёҠе·Із»Ҹе·ҘдҪңдәҶ3е№ҙжңүдҪҷгҖӮиҝҷ3е№ҙеӨҡйҮҢпјҢжұ—ж°ҙдёҺжІ№жұЎе°Ҷе·ҘиЈ…еҸҚеӨҚжөёйҖҸпјҢж— ж•°дёӘж—ҘеӨңпјҢжңәиҪҰйҡҶйҡҶеЈ°еңЁиҖіз•”дҪңе“ҚпјҢе®ғ们е…ұеҗҢзј–з»ҮдәҶжҲ‘йқ’жҳҘдёӯжңҖйҡҫеҝҳзҡ„зҜҮз« гҖӮ
гҖҖгҖҖеҲҡеҸӮеҠ е·ҘдҪңж—¶пјҢжҲ‘еҜ№еҶ…зҮғжңәиҪҰеҮ д№ҺдёҖж— жүҖзҹҘгҖӮеёҲеӮ…йўҶзқҖжҲ‘иө°иҝӣеҶ…зҮғжңәиҪҰжЈҖдҝ®еә“пјҢжҢҮзқҖзңјеүҚйӮЈеҸ°еәһеӨ§зҡ„еҶ…зҮғжңәиҪҰпјҢ笑зқҖиҜҙпјҡвҖңд»ҘеҗҺпјҢиҝҷйҮҢе°ұжҳҜдҪ зҡ„жҲҳеңәдәҶгҖӮвҖқйӮЈдёҖзһ¬й—ҙпјҢжҲ‘ж—ўе…ҙеҘӢеҸҲеҝҗеҝ‘гҖӮ
гҖҖгҖҖиө·еҲқпјҢжҲ‘зҡ„д»»еҠЎеҸӘжҳҜж“ҰжӢӯйӣ¶йғЁд»¶пјҢеҝғйҮҢиҝҳжңүдәӣдёҚз”ҳпјҢи§үеҫ—иҝҷдёҺжҲ‘жғіиұЎдёӯзҡ„жҠҖжңҜе·ҘдҪңзӣёеҺ»з”ҡиҝңгҖӮдҪҶеҪ“жҲ‘зңӢеҲ°еёҲеӮ…们жұ—жөҒжөғиғҢпјҢдё“жіЁең°жЈҖдҝ®жңәиҪҰзҡ„жҜҸдёҖдёӘз»ҶиҠӮпјҢйӮЈд»ҪеҜ№е·ҘдҪңзҡ„зғӯзҲұе’Ң敬дёҡж·ұж·ұи§ҰеҠЁдәҶжҲ‘гҖӮжҲ‘ж„ҸиҜҶеҲ°пјҢзңҹжӯЈзҡ„жҠҖжңҜе·ҘдҪң并дёҚжҳҜдёҖи№ҙиҖҢе°ұ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йңҖиҰҒд»ҺжңҖеҹәзЎҖеҒҡиө·пјҢдёҖзӮ№дёҖж»ҙең°з§ҜзҙҜз»ҸйӘҢе’ҢзҹҘиҜҶгҖӮ
гҖҖгҖҖи®°еҫ—еҺ»е№ҙдёҖдёӘеҜ’еҶ·зҡ„ж·ұеӨңпјҢдёҖеҸ°еҚіе°ҶеҸ‘иҪҰзҡ„вҖңе’Ңи°җ3BеһӢвҖқеҶ…зҮғжңәиҪҰзӘҒеҸ‘ж•…йҡңгҖӮжҲ‘е’ҢеҗҢдәӢ们еҮҢжҷЁдёӨзӮ№иө¶еҲ°зҺ°еңәпјҢжңәиҪҰжЈҖдҝ®еә“еҶ…еҚҙжҳҜдёҖзүҮзғӯзҒ«жңқеӨ©зҡ„жҷҜиұЎгҖӮжҲ‘иҙҹиҙЈжЈҖдҝ®жҹҙжІ№жңәвҖ”вҖ”йӮЈдёӘиў«иӘүдёәжңәиҪҰвҖңеҝғи„ҸвҖқзҡ„ж ёеҝғйғЁд»¶гҖӮеңЁйҖјд»„зҡ„з©әй—ҙйҮҢпјҢй«ҳжё©зғӯж°”жү‘йқўиҖҢжқҘпјҢжұ—ж°ҙеҫҲеҝ«жөёж№ҝдәҶиЎЈжңҚгҖӮеҮӯжҲ‘ж—Ҙеёёзҡ„з»ҸйӘҢеҲӨж–ӯпјҢжӯӨж—¶жҹҙжІ№жңәзӣ–е’ҢжІ№ж°ҙз®Ўи·Ҝзҡ„жё©еәҰеә”иҜҘдёҚдҪҺдәҺ70ж‘„ж°ҸеәҰгҖӮ
гҖҖгҖҖз”ұдәҺжҹҙжІ№жңәйғЁд»¶дёҺжңәиҪҰжІ№гҖҒж°ҙзӯүз®Ўи·ҜзӣёиҝһпјҢжІ№жұЎжІ№жіҘеҫҲеӨҡпјҢз©әй—ҙзӢӯе°ҸпјҢжҲ‘еҸӘиғҪеј“зқҖиә«еӯҗеңЁйҮҢйқўе·ҘдҪңгҖӮжІЎжңүзқҖеҠӣзӮ№пјҢеҫҲеҝ«пјҢжҲ‘зҡ„и…ҝи„ҡе°ұеғөзӣҙдәҶпјҢжүӢд№ҹй…ёз—ӣдёҚе·ІгҖӮз»ҸиҝҮдәүеҲҶеӨәз§’ең°з»ҶиҮҙжҺ’жҹҘпјҢжҲ‘з»ҲдәҺеҸ‘зҺ°дәҶж•…йҡңеҺҹеӣ пјҡиҶЁиғҖж°ҙз®ұеҮәж°ҙз®Ўзҡ„еҝ«йҖҹжҺҘеӨҙж №йғЁеҸ‘з”ҹдәҶжқҫеҠЁгҖӮйӮЈдёҖеҲ»пјҢжҲ‘зј“зј“иҲ’дәҶеҸЈж°”пјҢдҪҶжүӢеҚҙејӮеёёзЁіе®ҡең°иҝ…йҖҹжӣҙжҚўдәҶж–°жҺҘеӨҙ并зҙ§еӣәеҘҪгҖӮдҫ§иә«жҢӨеҮәжңәиҪҰжЈҖдҝ®й—ҙж—¶пјҢйӮЈдёҖеҲ»зҡ„жҲҗе°ұж„ҹе’ҢиҮӘиұӘж„ҹпјҢиҮід»Ҡи®©жҲ‘йҡҫд»ҘеҝҳжҖҖгҖӮ
гҖҖгҖҖж—¶й—ҙеҰӮжңәжІ№иҲ¬зј“зј“жөҒж·ҢпјҢеҰӮд»ҠпјҢжҲ‘д№ҹд»ҺйӮЈдёӘеҜ№дёҖеҲҮе……ж»ЎеҘҪеҘҮзҡ„ж–°жүӢпјҢжҲҗй•ҝдёәдёҖеҗҚиғҪеӨҹзӢ¬еҪ“дёҖйқўзҡ„йқ’е№ҙй’іе·ҘгҖӮжҲ‘зҹҘйҒ“пјҢжңӘжқҘзҡ„и·ҜиҝҳеҫҲй•ҝпјҢжҢ‘жҲҳиҝҳеҫҲеӨҡпјҢдҪҶжҲ‘зӣёдҝЎпјҢеҸӘиҰҒжҲ‘дҝқжҢҒзқҖеҜ№е·ҘдҪңзҡ„зғӯзҲұе’ҢеҜ№жҠҖжңҜзҡ„иҝҪжұӮпјҢе°ұдёҖе®ҡиғҪеӨҹе…ӢжңҚдёҖеҲҮеӣ°йҡҫпјҢиө°еҫ—жӣҙиҝңгҖӮпјҲеҙ”жәҰжәҰ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е®ҲеңЁй»„йҫҷд№қеҜЁз«ҷ
гҖҖгҖҖзҹіеҫ·пјҲи—Ҹж—ҸпјҢ32еІҒпјүй»„йҫҷд№қеҜЁз«ҷе®ўиҝҗеҖјзҸӯе‘ҳ
гҖҖгҖҖжҲ‘жӣҫж— ж•°ж¬Ўең°е№»жғіпјҢй«ҳй“ҒејҖеҲ°жҲ‘зҡ„家乡йҳҝеққдјҡжҳҜжҖҺж ·зҡ„дёҖз§ҚеңәжҷҜгҖӮ
гҖҖгҖҖеңЁе·қйқ’й“Ғи·Ҝй•Үй»„ж®өејҖйҖҡеҗҺпјҢйҳҝеққеҗёеј•дәҶе…Ёзҗғзҡ„е…іжіЁпјҢй»„йҫҷд№қеҜЁз«ҷдёҖејҖйҖҡдҫҝжҲҗдёәвҖңйЎ¶жөҒвҖқпјҢзңӢзқҖејҖиҝӣ家乡зҡ„дёҖиҫҶиҫҶзҒ«иҪҰе’Ңз»ңз»ҺдёҚз»қзҡ„ж—…е®ўпјҢжӣҫе№»жғіиҝҮж— ж•°ж¬Ўзҡ„еңәжҷҜз«ҹзңҹзҡ„еҮәзҺ°еңЁдәҶжҲ‘зңјеүҚ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еңҹз”ҹеңҹй•ҝзҡ„и—Ҹж—Ҹ姑еЁҳпјҢ2023е№ҙе·қйқ’й“Ғи·Ҝйқ’зҷҪжұҹиҮій•Үжұҹе…іж®өејҖйҖҡеҗҺпјҢжҲ‘е°ұеӣһеҲ°дәҶ家乡йҳҝеққе·ҘдҪңгҖӮе·ҘдҪңең°д»ҺжңҖејҖе§Ӣзҡ„й•Үжұҹе…із«ҷеҲ°зҺ°еңЁзҡ„й»„йҫҷд№қеҜЁз«ҷпјҢд»Һжө·жӢ”2503зұіеҲ°2977зұіпјҢжҲ‘еҜ№жңӘжқҘе·ҘдҪңзҡ„жҶ§жҶ¬дёҺжңҹеҫ…д№ҹйҡҸзқҖжө·жӢ”зҡ„еўһй«ҳеҸҳеҫ—и¶ҠеҸ‘й«ҳж¶ЁгҖӮ
гҖҖгҖҖеҲҡеҲ°й»„йҫҷд№қеҜЁз«ҷж—¶пјҢиҪҰз«ҷеҹәзЎҖи®ҫж–ҪиҝҳжІЎе®Ңе·ҘпјҢжҲ‘们иҰҒжҸҗзқҖеӨ§жЎ¶еҲ°еІ·жұҹж—ҒеҸ–ж°ҙпјҢд»Ҙи§ЈеҶіж—Ҙеёёз”Ёж°ҙй—®йўҳгҖӮз”Ёз”өд№ҹжҳҜйҡҫйўҳпјҢдёҖеҲ°жҷҡдёҠж•ҙдёӘиҪҰз«ҷиў«й»‘еӨңз¬јзҪ©пјҢеҘіеҗҢдәӢ们е°ұжҢӨеңЁдёҖдёӘжҲҝй—ҙйҮҢдј‘жҒҜгҖҒиҒҠеӨ©пјҢжҶ§жҶ¬зқҖејҖйҖҡеҗҺзҡ„ж—ҘеӯҗгҖӮиҒ”и°ғиҒ”иҜ•жңҹй—ҙпјҢйЈҹе Ӯд№ҹиҝҳжІЎе®Ңе·ҘпјҢеӨ§е®¶иҝҳиҰҒиҮӘе·ұеҠЁжүӢеҒҡйҘӯгҖӮ
гҖҖгҖҖд»Ҡе№ҙжҳҜжҲ‘们иҪҰз«ҷзҡ„йҰ–ж¬ЎжҳҘиҝҗпјҢж—…е®ўиҝҗиҫ“з»„з»Үе·ҘдҪңиҝңжҜ”жғіиұЎдёӯеӨҚжқӮгҖӮжҲ‘们ж•ҙж—ҘеңЁдәәжҪ®дёӯз©ҝжўӯпјҢеңЁе°Ҹе°Ҹзҡ„иҪҰз«ҷйҮҢдёҖеӨ©иғҪиө°дёҠдёҮжӯҘгҖӮеҸҲжҒ°е·§йҒҮдёҠдәҶй«ҳеҺҹеҶ°йӣӘеҮқеҶ»еӨ©ж°”пјҢеӨңйҮҢдёӢжҡҙйӣЁжҡҙйӣӘпјҢжҲ‘们еҮҢжҷЁе°ұеҫ—йҷӨеҶ°жү«йӣӘгҖҒй“әйҳІж»‘еһ«пјҢе…ЁеҠӣдҝқйҡңж—…е®ўе®үе…ЁеҮәиЎҢгҖӮ
гҖҖгҖҖеҠЁиҪҰ驶е…Ҙ家乡пјҢз©әж°”йғҪејҘжј«зқҖе№ёзҰҸзҡ„иҠ¬иҠігҖӮ家дәәдёәжҲ‘иҮӘиұӘпјҢд№ЎдәІд»¬д№ҹиғҪд№ҳзҒ«иҪҰеҮәеұұзңӢдё–з•ҢгҖӮеңЁз»өйҳіиҪҰеҠЎж®өжӢ…д»»и°ғеәҰе‘ҳзҡ„вҖңејӮең°жҒӢвҖқдёҲеӨ«пјҢд№ҹе§Ӣз»Ҳе…ЁеҠӣж”ҜжҢҒжҲ‘пјҢиҷҪиҒҡе°‘зҰ»еӨҡпјҢдҪҶжҲ‘们зӣёдә’зҗҶи§ЈпјҢе°ҶзҲұдёҺжҖқеҝөеҜ„дәҲй“ҒиҪЁ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жңҖзҲұй«ҳеҺҹж јжЎ‘иҠұпјҢж„ҝеҰӮе®ғдёҖиҲ¬еқҡйҹ§зҫҺдёҪпјҢж·ұж·ұжүҺж №иҝҷзүҮеңҹең°пјҢз»ҳе°ұе·қйқ’зҫҺеҘҪж–°еӣҫжҷҜгҖӮ пјҲйӮ“ж–Үй‘«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еўһж·»иҝҮиүІеҪ©дҫҝеҜ№еҫ—иө·иҝҷж—ҘеӨң
гҖҖгҖҖзҺӢеӨ©е…ҙпјҲ28еІҒпјүдәҢиҝһзҒ«иҪҰз«ҷдҝ„иҜӯзҝ»иҜ‘
гҖҖгҖҖ7е№ҙжңүеӨҡй•ҝпјҹжҳҜ3е№ҙй«ҳдёӯе’Ң4е№ҙеӨ§еӯҰж—¶е…үзҡ„жҖ»е’ҢпјҢд№ҹжҳҜжҲ‘еҸӮеҠ е·ҘдҪңзҡ„жҖ»ж—¶й•ҝгҖӮи®°еҫ—жҜ•дёҡзҡ„йӮЈе№ҙпјҢжҲ‘жҖҖзқҖеҝҗеҝ‘е’Ңе…ҙеҘӢзҡ„еҝғжғ…еқҗдёҠдәҶеҺ»еҶ…и’ҷеҸӨзҡ„зҒ«иҪҰпјҢд»Һзҹіе®¶еә„еҲ°е‘је’Ңжө©зү№пјҢеҶҚд»Һе‘је’Ңжө©зү№еҲ°дәҢиҝһжө©зү№пјҢд»ҺеӨ©дә®еҲ°еӨ©й»‘пјҢеҶҚеҲ°еӨ©дә®пјҢдјҙйҡҸзқҖеҲ—иҪҰзҡ„жҸҗзӨәйҹіпјҢжҲ‘иёҸдёҠдәҶиҝҷзүҮйҷҢз”ҹеҸҲиҚ’еҮүзҡ„еӨ§ең°гҖӮ
гҖҖгҖҖеӣ дёәд»Һе°ҸеңЁзҹіе®¶еә„й•ҝеӨ§пјҢеҪ“ж—¶зҡ„жҲ‘еҜ№еҶ…и’ҷеҸӨзҡ„дёҖеҲҮе……ж»ЎдәҶеҘҪеҘҮпјҢе’ёе‘ізҡ„еҘ¶иҢ¶пјҢзәўжұӨзҡ„зҫҠжқӮпјҢжӢ—еҸЈзҡ„ж–№иЁҖпјҢд»ҘеҸҠе…Ёж–°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ҚҠи·ҜеҮә家зҡ„вҖңеҮҶй“Ғи·ҜдәәвҖқпјҢжҺҘеҲ°з”өиҜқиҜўй—®вҖңжӢҗе…«е№әжӢҗвҖқйӮЈи¶ҹиҪҰ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дёҖеӨҙйӣҫж°ҙгҖӮеёҲеӮ…и·ҹжҲ‘и§ЈйҮҠеҗҺпјҢжҲ‘жүҚжҳҺзҷҪжҳҜеңЁй—®7817ж¬ЎеҲ—иҪҰпјҢдәҺжҳҜжҲ‘ејҖе§Ӣз–ҜзӢӮеӯҰд№ е…ідәҺй“Ғи·Ҝзҡ„дёҖеҲҮгҖӮж…ўж…ўең°пјҢи®°еҝҶдёӯзҡ„дҝ„иҜӯдё“дёҡзҹҘиҜҶиў«жҲ‘ж·ЎеҝҳпјҢж—ҘеӯҗдёҖеӨ©еӨ©иҝҮеҺ»пјҢжҲ‘йҷ·е…ҘдәҶе®үйҖёзҡ„вҖңеңҲеҘ—вҖқдёӯгҖӮ
гҖҖгҖҖиҷҪ然жҲ‘жҳҜеҢ—ж–№дәәпјҢдҪҶд»ҺжқҘжІЎжғіеҲ°дәҢиҝһжө©зү№зҡ„еҶ¬еӨ©еҰӮжӯӨеҜ’еҶ·пјҢеҮӣеҶҪзҡ„еҜ’йЈҺеҗ№еғөдәҶжҲ‘зҡ„и„ёеәһпјҢд№ҹеҗ№ж•ЈдәҶжҲ‘зҡ„й“Ғи·ҜжўҰгҖӮйӮЈж—¶еҖҷжҲ‘жүҚж„ҸиҜҶеҲ°пјҢеңЁеҸЈеІёе·ҘдҪңзҡ„ж—Ҙ常并дёҚжҳҜжҲ‘жғіиұЎзҡ„йӮЈж ·пјҢжё©еәҰдёҖеӨ©еӨ©йҷҚдҪҺпјҢжҲ‘зҡ„еҝғд№ҹдёҖеӨ©жҜ”дёҖеӨ©еҮүпјҢеҲәйӘЁзҡ„еҜ’йЈҺпјҢеҶ—жқӮ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ж— дәәзҡ„еӨңйҮҢжҲ‘еҜ№зқҖз”өи„‘ж•ІеҮ»зқҖй”®зӣҳпјҢйў‘йў‘еҚ—жңӣпјҢеҚҙд№ҹиҝҲдёҚејҖи…ҝйҖғеҮәиҝҷеҢ—ж–№гҖӮ
гҖҖгҖҖзҰ»е®¶зҡ„дәәеҝғйҮҢжҖ»жҳҜжҶӢзқҖдёҖеҸЈж°”пјҢжғіж··еҮәдёӘж ·пјҢжғіи®©е®¶йҮҢдәәи§үеҫ—иҮӘе·ұиғҪиҝҮеҫ—еҫҲеҘҪгҖӮдёҖеӨ©жҷҡдёҠжҲ‘з»ҷ家йҮҢжӢЁдәҶдёӘз”өиҜқпјҢжғіиҜҙиҜҙиҮӘе·ұзҡ„иӢҰй—·пјҢиҜқеҲ°еҳҙиҫ№еҸҲе’ҪдәҶдёӢеҺ»пјҢжІЎеҮ еҸҘе°ұжІүй»ҳдәҶпјҢз”өиҜқжІЎжңүжҢӮпјҢдҪҶ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иҜҙдәӣд»Җд№ҲгҖӮиүҜд№…пјҢзҲ¶дәІзҡ„еЈ°йҹід»ҺжүӢжңәйҮҢдј жқҘпјҡвҖңе…¶е®һжҲ‘们д№ҹжІЎжғіеҲ°дҪ иғҪеҲ°й“Ғи·Ҝе·ҘдҪңпјҢиҰҒжҳҜеҫ…еҫ—дёҚд№ жғҜе°ұеӣһжқҘеҗ§гҖӮвҖқжҲ‘дҪҜиЈ…й•Үе®ҡиҜҙдәҶеҸҘвҖңзҹҘйҒ“дәҶвҖқе°ұеҢҶеҢҶжҢӮдәҶз”өиҜқпјҢйӮЈдёҖжҷҡжҲ‘жғідәҶеҫҲеӨҡгҖӮ
гҖҖгҖҖ第дәҢеӨ©пјҢеҪ“жҲ‘еҶҚйҶ’жқҘж—¶пјҢжҲ‘еҶіе®ҡеҝ…йЎ»ж”№еҸҳиҮӘе·ұпјҢи®©иҮӘе·ұеҺ»йҖӮеә”иҝҷдёҖеҲҮгҖӮжҲ‘д»”з»Ҷзҝ»иҜ‘зқҖиҝҗеҚ•дёҠжҜҸдёҖж Ҹзҡ„еҶ…е®№пјҢеңЁз¬”и®°жң¬дёҠи®°еҪ•зқҖеёёи§Ғзҡ„е“ҒеҗҚгҖҒеҸ‘еҲ°з«ҷзӯүгҖӮж”№еҸҳжңҖйҡҫзҡ„е°ұжҳҜиёҸеҮәиҝҷдёҖжӯҘпјҢиҖҢиёҸеҮәиҝҷдёҖжӯҘеҗҺпјҢж•°жҚ®д№ҹдёҚжҳҫеҫ—йӮЈд№ҲеҶ—жқӮпјҢжҜҸж¬ЎеҪ•е…Ҙе®Ңж ёеҜ№жӯЈзЎ®еҗҺе°ұеғҸжү“дәҶиғңд»—дёҖж ·гҖӮеҪ“жҲ‘зңҹжӯЈе…Ёиә«еҝғжҠ•е…Ҙе·ҘдҪңдёӯпјҢдёҖеҲҮйғҪеҸҳеҫ—иұҒ然ејҖжң—пјҢжҜҸдёҖеӨ©зҡ„е·ҘдҪңд№ҹдёҚеҶҚе……ж»ЎжҠұжҖЁгҖӮе°ұиҝҷж ·жҲ‘иҝҺжқҘдәҶе’ҢдәҢиҝһиҪҰз«ҷзҡ„第7е№ҙпјҢдёҖе№ҙдёҖе№ҙзҡ„еқҡе®ҲпјҢи®©вҖңжүҺж №иҫ№з–ҶпјҢеҘүзҢ®жӢ…еҪ“вҖқдёҚеҶҚеҸӘжҳҜдёҖеҸҘеҸЈеҸ·гҖӮ
гҖҖгҖҖ28еІҒзҡ„жҲ‘пјҢеҰӮд»Ҡд№ҹжҳҜд»–дәәзҡ„еёҲеӮ…гҖӮзңӢзқҖдёҖдёӘдёӘеҲҡе…ҘиҒҢзҡ„вҖңиҗҢж–°вҖқпјҢжҲ‘ж„ҸиҜҶеҲ°пјҢжҲ‘зҡ„йқ’жҳҘе·Із»Ҹз•ҷеңЁдәҶиҝҷеә§е°ҸеҹҺгҖӮдё–дёҠе“Әжңүеёёйқ’ж ‘пјҢжҲ‘жӣҫдёәиҝҷеә§еҹҺеёӮеўһж·»иҝҮиүІеҪ©пјҢйӮЈдҫҝеҜ№еҫ—иө·иҝҷж—ҘеӨңгҖӮпјҲдәҺжҷЁ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”
гҖҖгҖҖз”ЁйҮҚиҪҪйҖҹеәҰе®ҲжҠӨж°‘з”ҹжё©еәҰ
гҖҖгҖҖзЁӢеҝ—дјҹпјҲ28еІҒпјүж№–дёңз”өеҠӣжңәеҠЎж®өйҮҚиҪҪеҸёжңә
гҖҖгҖҖжҲ‘жүҖеҖјд№ҳзҡ„еӨ§з§Ұй“Ғи·Ҝе…Ёй•ҝ653е…¬йҮҢпјҢиҘҝиө·еҸӨйғҪеӨ§еҗҢпјҢз©ҝи¶ҠзҮ•еұұгҖҒи·ЁиҝҮжЎ‘е№ІжІіпјҢзӣҙжҠөжёӨжө·д№Ӣж»ЁпјҢж”Ҝж’‘зқҖе…ЁеӣҪеӣӣеӨ§з”өзҪ‘гҖҒдә”еӨ§еҸ‘з”өйӣҶеӣўгҖҒеҚҒеӨ§й’ўй“Ғе…¬еҸёе’Ңж•°д»ҘдёҮи®Ўзҡ„е·ҘзҹҝдјҒдёҡд»ҘеҸҠеҚҒеҮ дёӘзңҒгҖҒиҮӘжІ»еҢәгҖҒзӣҙиҫ–еёӮзҡ„з”ҹдә§з”ҹжҙ»з”Ёз…ӨпјҢиў«иӘүдёәвҖңдёӯеӣҪйҮҚиҪҪ第дёҖи·Ҝ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д»Ҡе№ҙжҳҜжҲ‘жүҺж №еӨ§з§Ұй“Ғи·Ҝзҡ„第5дёӘжҳҘиҝҗпјҢдёҺеҫҖе№ҙдёҚеҗҢзҡ„жҳҜпјҢеҰӮд»ҠпјҢжҲ‘е·Із»ҸеҰӮж„ҝжҲҗй•ҝдёәдёҖеҗҚдёӨдёҮеҗЁйҮҚиҪҪеҲ—иҪҰдё»жҺ§еҸёжңәгҖӮе…ЁеӣҪеғҸжҲ‘дёҖж ·е…·жңүй©ҫ驶иҝҷз§ҚйҮҚиҪҪеҲ—иҪҰиө„иҙЁзҡ„еҸёжңәеҸӘжңү600дҪҷдәәпјҢжңүдәәиҜҙжҲ‘们жҳҜвҖңиҲһйҫҷдәәвҖқ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иҝҷжқЎвҖңе·ЁйҫҷвҖқжҳҜдёҖжқЎиҪҪйҮҚдёӨдёҮеҗЁгҖҒй•ҝеәҰеҸҜд»ҘиҫҫеҲ°2.6е…¬йҮҢзҡ„йҮҚиҪҪеҲ—иҪҰгҖӮ
гҖҖгҖҖ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е№іеқҮжҜҸ12еҲҶй’ҹе°ұдјҡ驶еҮәдёҖеҲ—ж»ЎиҪҪз…ӨзӮӯзҡ„дёӨдёҮеҗЁйҮҚиҪҪеҲ—иҪҰпјҢеҰӮеҗҢдёҖжқЎжөҒж·Ңзҡ„вҖңз…ӨжІівҖқпјҢж—ҘеӨңдёҚжҒҜгҖӮеёҲеӮ…们常常е’Ң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ејҖйҮҚиҪҪеҲ—иҪҰдёҚж•ўжңүеҚҠзӮ№й©¬иҷҺпјҢеӣ дёәиҝҷжқЎи·ҜпјҢдёҖеӨҙиҝһзқҖ家пјҢдёҖеӨҙиҝһзқҖеӣҪ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Ө§з§Ұй“Ғи·ҜдёңиҘҝжө·жӢ”иҗҪе·®дёҠеҚғзұіпјҢй•ҝеӨ§еқЎйҒ“иҝ‘зҷҫе…¬йҮҢпјҢејҜйҒ“дёҠеҚғеӨ„пјҢеңЁе…ій”®еҢәж®өеҶ…пјҢиҝҷеҲ—з”ұ210иҠӮиҪҰиҫҶз»„жҲҗгҖҒй•ҝиҫҫ2.6е…¬йҮҢзҡ„еҲ—иҪҰеӨҙйғЁе°ҫйғЁзҡ„зәөеҗ‘жө·жӢ”иҗҪе·®жңү31.4зұіпјҢзӣёеҪ“дәҺ10еұӮжҘјзҡ„й«ҳеәҰгҖӮеҜ№дәҺйҮҚиҪҪеҸёжңәиҖҢиЁҖпјҢжҜҸдёҖж¬ЎеҲ¶еҠЁгҖҒи°ғйҖҹйғҪдҪҝе‘ҪйҮҚеӨ§пјҢдёҚд»…йңҖиҰҒжү§иЎҢ300еӨҡйЎ№ж ҮеҮҶеҢ–ж“ҚдҪңжөҒзЁӢпјҢиҝҳиҰҒеҜ№жҜҸдёҖж®өеқЎйҒ“гҖҒжҜҸдёҖйЎ№ж•°жҚ®гҖҒжҜҸдёҖдёӘжүӢеҠҝгҖҒжҜҸдёҖдёӘдҝЎеҸ·зғӮзҶҹдәҺеҝғпјҢжӣҙиҰҒеҜ№жүӢдёӯзҡ„жүӢжҹ„ж“ҚзәөеҒҡеҲ°з»қеҜ№зІҫеҮҶгҖӮ
гҖҖгҖҖвҖң4дәҝеҗЁгҖҒ130дёҮеҗЁгҖҒ54000еҗЁгҖҒ902еҗЁгҖҒ15еҗЁвҖҰвҖҰвҖқиҝҷдёҖдёІж•°еӯ—д»ЈиЎЁзҡ„жҳҜеӨ§з§Ұй“Ғи·ҜжҜҸе№ҙгҖҒжҜҸеӨ©гҖҒжҜҸж—¶гҖҒжҜҸеҲҶгҖҒжҜҸз§’зҡ„з…ӨзӮӯиҝҗйҮҸгҖӮжӣҫжңүдәәжөӢз®—пјҢеңЁйҰ–йғҪеҢ—дә¬пјҢе№іеқҮжҜҸ6зӣҸзҒҜдёӯе°ұжңүдёҖзӣҸзҒҜжҳҜйқ еӨ§з§Ұй“Ғи·Ҝзҡ„иҝҗиҫ“жүҖзӮ№дә®зҡ„гҖӮжӯЈжҳҜж— ж•°йҮҚиҪҪеҸёжңәзҡ„жӢјжҗҸеҘүзҢ®гҖҒж—ҘеӨңе…јзЁӢпјҢз”ЁйҮҚиҪҪйҖҹеәҰе®ҲжҠӨж°‘з”ҹжё©еәҰпјҢз”Ёйқ’жҳҘжӢ…еҪ“жҠӨеҚ«дёҮйҮҢеҪ’йҖ”пјҢжүҚиғҪи®©ж°‘з”ҹжңүжё©еәҰпјҢи®©е№ёзҰҸжңүиҙЁж„ҹпјҢдёә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жәҗжәҗдёҚж–ӯең°вҖңиҫ“иғҪвҖқгҖӮпјҲйҹ©ж¶ӣ ж•ҙзҗҶпјү
гҖҖгҖҖжқҘжәҗпјҡ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
гҖҖгҖҖ2025е№ҙ02жңҲ17ж—Ҙ 07зүҲ





 дә¬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 11010102004843еҸ·
дә¬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 11010102004843еҸ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