жңүдәәдёәж— дәәжңәиЎЁжј”еҒҡеҜјжј” жңүдәәзӢ¬з«ӢејҖеҸ‘App жңүдәәдёәвҖңйҖҸжҳҺеҝғи„ҸвҖқе»әжЁЎ
иҝҷдәӣзӮ«й…·ж–°иҒҢдёҡ й…Қеҫ—дёҠе№ҙиҪ»дәәзҡ„йҮҺеҝғ
еҸ‘зЁҝж—¶й—ҙпјҡ2025-11-18 09:49:00 зј–иҫ‘пјҡжқҺ婧жҖЎ жқҘжәҗпјҡ еҢ—дә¬йқ’е№ҙжҠҘ

гҖҖгҖҖAIеҠЁз”»еёҲеҗҙз‘•

гҖҖгҖҖжқҺжҳҹдҪ‘пјҲе·ҰдёҖпјүе’Ңеә“е…ӢеҗҲеҪұ

гҖҖгҖҖж— дәәжңәзј–йҳҹеёҲеҲҳдҪіжҳ•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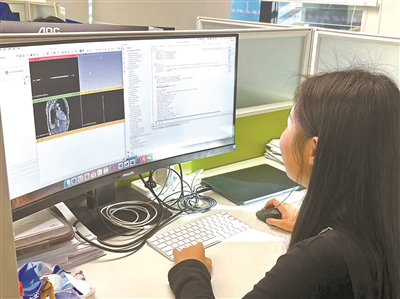
гҖҖгҖҖе·ҘдҪңдёӯзҡ„иӢҸеӯҗиҙӨ

гҖҖгҖҖеҗҙз‘•еҲ©з”ЁAIеҲӣдҪңзҡ„зҫҺжңҜдҪңе“Ғ
гҖҖгҖҖеңЁжҲ‘们иә«иҫ№пјҢиҒҢдёҡзҡ„ж ·иІҢжӯЈеңЁжӮ„然改еҸҳгҖӮиҝҮеҺ»дёҖдәӣеҗ¬иө·жқҘжңүдәӣвҖң科幻вҖқ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еҰӮд»ҠжӯЈжҲҗдёәи®ёеӨҡе№ҙиҪ»дәәеҘӢж–—зҡ„ж–°йўҶеҹҹгҖӮ
гҖҖгҖҖ他们еҸҜиғҪдёҚеғҸдј з»ҹ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дёҠзҸӯж—ҸпјҡжңүдәәжҳҜж— дәәжңәзј–йҳҹеёҲпјҢд»–зҡ„е·ҘдҪңжҳҜеңЁж·ұеӨңзҡ„е№ҝеңәдёҠпјҢдё“жіЁең°и°ғиҜ•зЁӢеәҸ;жңүдәәжҳҜAIеҠЁз”»еёҲпјҢд»–дёҚеҶҚйңҖиҰҒдёҖ笔дёҖ笔ең°з”»пјҢиҖҢжҳҜдёҚж–ӯвҖңе–Ӯе…»вҖқе’Ңи®ӯз»ғAIе®ҢжҲҗж»Ўж„Ҹзҡ„дҪңе“ҒпјӣиҝҳжңүдәәпјҢйҖүжӢ©еңЁе°Ҹе°Ҹзҡ„жүӢжңәеұҸ幕дёҠејҖеҲӣиҮӘе·ұзҡ„дәӢдёҡпјҢдёәдёҖдёӘAppзҡ„еҠҹиғҪи®ҫи®ЎеҸҚеӨҚжҖқиҖғпјӣеңЁе®һйӘҢе®ӨжҲ–з”өи„‘еүҚпјҢAIз®—жі•з ”з©¶е‘ҳ们еҲҷеңЁиҜ•еӣҫйҖҡиҝҮеҗ„з§Қж–№жі•и®©жңәеҷЁеҸҳеҫ—жӣҙвҖңиҒӘжҳҺвҖқдёҖзӮ№вҖҰвҖҰ
гҖҖгҖҖиҝҷдәӣз”ұж–°жҠҖжңҜеӮ¬з”ҹ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жӯЈеңЁдёәе№ҙиҪ»дәәжҺЁејҖдёҖжүҮж–°зҡ„иҒҢдёҡеӨ§й—ЁпјҢ并е®һе®һеңЁеңЁең°еҲӣйҖ д»·еҖјгҖӮ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йҮҚиҰҒзҡ„дёҚд»…жҳҜеӯҰеҺҶпјҢжӣҙжҳҜеҲӣж–°ж„ҸиҜҶгҖҒеӯҰд№ иғҪеҠӣпјҢд»ҘеҸҠе°Ҷжғіжі•д»ҳиҜёе®һи·өзҡ„еӢҮж°”гҖӮйҖҡиҝҮ他们пјҢжҲ–и®ё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з§‘еҲӣж—¶д»ЈпјҢе№ҙиҪ»дәәзҡ„ж–°иҒҢдёҡж–°йҖүжӢ©гҖӮ
гҖҖгҖҖAIеҠЁз”»еёҲ
гҖҖгҖҖдёҖдёӘдәәйЎ¶дёҠдёҖдёӘеӣўйҳҹ
гҖҖгҖҖеҸӘйңҖиҫ“е…ҘеҮ иЎҢжҸҸиҝ°пјҢдәәе·ҘжҷәиғҪдҫҝиғҪеңЁеҮ еҲҶй’ҹеҶ…з”ҹжҲҗдёҖж®өе……ж»ЎжғіиұЎеҠӣзҡ„зҹӯи§Ҷйў‘гҖӮиҝҷ并йқһ科幻еңәжҷҜпјҢиҖҢжҳҜAIGCпјҲдәәе·ҘжҷәиғҪз”ҹжҲҗеҶ…е®№пјүеҲӣдҪңиҖ…зҡ„ж—ҘеёёгҖӮеҗҙз‘•пјҢдёҖдҪҚд»Һдј з»ҹжёёжҲҸиЎҢдёҡжҲҗеҠҹиҪ¬еһӢзҡ„е…ҲиЎҢиҖ…пјҢжӯЈжҙ»и·ғдәҺиҝҷдёӘж–°е…ҙзҡ„йўҶеҹҹгҖӮ
гҖҖгҖҖ1985е№ҙеҮәз”ҹзҡ„еҗҙз‘•жҜ•дёҡдәҺиҮӘеҠЁеҢ–дё“дёҡпјҢиҒҢдёҡз”ҹж¶Ҝиө·жӯҘдҫҝеңЁжө·еӨ–дёҖ家зҹҘеҗҚжёёжҲҸе…¬еҸёгҖӮдҪңдёәж•°еӯ—иүәжңҜеёҲпјҢд»–еҸӮдёҺдәҶеӨҡдёӘеӨҮеҸ—иөһиӘүзҡ„йЎ№зӣ®гҖӮйҡҸеҗҺпјҢд»–еңЁеӣҪеҶ…жёёжҲҸгҖҒж•ҷиӮІзӯүеӨҡдёӘеҲӣж„Ҹдә§дёҡдёӯдёҚж–ӯиҪ¬еһӢжҺўзҙўгҖӮ2022е№ҙдёҺAIз»ҳз”»е·Ҙе…·зҡ„вҖңеҒ¶з„¶йӮӮйҖ…вҖқпјҢдёәд»–жү“ејҖдәҶеҸҰдёҖжүҮй—ЁгҖӮ
гҖҖгҖҖзңҹжӯЈзҡ„иҪ¬еҸҳеҸ‘з”ҹеңЁ2024е№ҙпјҢйҡҸзқҖеҸҜзҒөдёәйҰ–зҡ„еӣҪеҶ…AIи§Ҷйў‘е·Ҙе…·зҡ„жҲҗзҶҹпјҢAIи§Ҷйў‘ж„ҲеҸ‘зЁіе®ҡпјҢеҸҷдәӢж„ҲеҸ‘е®Ңж•ҙпјҢеҗҙз‘•ејҖе§Ӣз”Ёе…¶еҸӮдёҺе®һйҷ…йЎ№зӣ®дәӨд»ҳгҖӮд»–ж„ҸиҜҶеҲ°пјҡвҖңеҺҹжқҘеҖҹеҠ©AI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е°ұиғҪе®ҢжҲҗиҝҮеҺ»йңҖиҰҒдёҖдёӘеӣўйҳҹжүҚиғҪе®ҢжҲҗзҡ„е•ҶдёҡйЎ№зӣ®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д»–зҡ„йҰ–дёӘAIе•Ҷдёҡи®ўеҚ•жқҘиҮӘжёёжҲҸиЎҢдёҡзҡ„еҸӢдәәпјҢд»»еҠЎжҳҜдёәзҹҘеҗҚIPеҲ¶дҪңе®Јдј зүҮгҖӮд»ҺеҲҶй•ңеҲ°жҲҗзүҮпјҢе…ЁзЁӢз”ұAIеҸӮдёҺе®ҢжҲҗпјҢд»…з”ЁдёҖе‘ЁдҫҝйЎәеҲ©дәӨд»ҳгҖӮйҡҸзқҖдҪңе“ҒеңЁзӨҫдәӨе№іеҸ°зҡ„еұ•зӨәпјҢ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еҗҲдҪңйӮҖзәҰзә·иҮіжІ“жқҘпјҢе…¶дёӯж—ўжңүеӣҪеҶ…еӨҡ家主жөҒеӘ’дҪ“пјҢеҸҲжңүи®ёеӨҡеӣҪеҶ…еӨ–е“ҒзүҢдјҒдёҡгҖӮ
гҖҖгҖҖеҗҙз‘•еҗ‘еҢ—дә¬йқ’е№ҙжҠҘи®°иҖ…еұ•зӨәдәҶд»–зҡ„еҲӣдҪңжөҒзЁӢпјҡAIеӨ§жЁЎеһӢж’°еҶҷи„ҡжң¬гҖҒжҷәиғҪдҪ“з”ҹжҲҗеҲҶй•ңгҖҒзі»з»ҹвҖңжҠҪеҚЎвҖқдә§еҮәи§Ҷйў‘зҙ жқҗпјҢжңҖеҗҺиҝӣиЎҢдәәе·ҘеүӘиҫ‘дёҺзӯӣйҖүгҖӮвҖңжөҒзЁӢжЎҶжһ¶дёҺдј з»ҹеҲ¶дҪңзӣёдјјпјҢдҪҶAIжһҒеӨ§ең°зј©зҹӯдәҶдёӯй—ҙзҺҜиҠӮпјҢвҖқд»–и§ЈйҮҠйҒ“пјҢвҖңеҰӮд»Ҡ70%иҮі80%зҡ„е·ҘдҪңеҸҜз”ұAIе®ҢжҲҗпјҢжҲ‘们еҲҷжӣҙдё“жіЁдәҺеүҚжңҹзҡ„еҲӣж„Ҹе®ҡи°ғдёҺжңҖз»Ҳзҡ„е®ЎзҫҺжҠҠжҺ§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иҝҷз§Қж–°жЁЎејҸеёҰжқҘжҳҫи‘—ж•ҲзҺҮжҸҗеҚҮгҖӮжҚ®д»–дј°з®—пјҢеңЁи§Ҷйў‘еҲ¶дҪңйўҶеҹҹпјҢAIдҪҝеҫ—еҚ•дәәиғҪе®ҢжҲҗд»ҘеҫҖдә”е…ӯдёӘдәәеӣўйҳҹзҡ„е·ҘдҪңйҮҸпјҢжҲҗжң¬еӨ§е№…йҷҚдҪҺгҖӮиҝҷдёҚд»…ж”№еҸҳдәҶд»–зҡ„дёҡеҠЎз»“жһ„вҖ”вҖ”AIGCеҲӣдҪңеёҰжқҘзҡ„收е…Ҙе·Іи¶…иҝҮе°ҡеңЁз ”еҸ‘йҳ¶ж®өзҡ„дј з»ҹжёёжҲҸдёҡеҠЎпјҢд№ҹйҮҚеЎ‘дәҶиҒҢдёҡеҪўжҖҒгҖӮвҖңи®ёеӨҡжңүиғҪеҠӣзҡ„еҲӣдҪңиҖ…дёҚеҶҚеұҖйҷҗдәҺвҖҳеқҗзҸӯвҖҷпјҢ他们жӣҙеҖҫеҗ‘дәҺзәҝдёҠеҚҸдҪңдёҺиҮӘз”ұиҒҢдёҡпјҢиҝҪжұӮжӣҙиҮӘдё»зҡ„е·ҘдҪңиҠӮеҘҸ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Ҫ“иў«й—®еҸҠAIGCж—¶д»Јзҡ„ж ёеҝғз«һдәүеҠӣж—¶пјҢеҗҙз‘•ејәи°ғпјҡвҖңеҲӣж„ҸдёҺе®ЎзҫҺжүҚжҳҜе…ій”®гҖӮвҖқд»–и®ӨдёәпјҢAIйҷҚдҪҺдәҶжҠҖжңҜй—Ёж§ӣпјҢдҪҝжҜҸдёӘжҷ®йҖҡдәәйғҪиғҪжҲҗдёәеҲӣдҪңиҖ…пјҢдҪҶиҝҷ并дёҚж„Ҹе‘ізқҖжҠҖжңҜеЈҒеһ’зҡ„ж¶ҲеӨұвҖ”вҖ”вҖңзңӢдјјжІЎжңүй—Ёж§ӣпјҢе®һеҲҷеҜ№еҲӣдҪңиҖ…зҡ„еҲӣж„Ҹе’Ңе®ЎзҫҺжҸҗеҮәдәҶжӣҙй«ҳиҰҒжұӮ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AppзӢ¬з«ӢејҖеҸ‘иҖ…
гҖҖгҖҖеңЁд»Јз ҒдёӯеҘ”иөҙиҮӘе·ұзҡ„зғӯзҲұ
гҖҖгҖҖ1999е№ҙеҮәз”ҹзҡ„жқҺжҳҹдҪ‘пјҢеңЁеӨ§еҺӮе·ҘдҪңдәҶ5е№ҙпјҢжӢҝеҲ°з§»еҠЁеә”з”ЁеҲӣж–°иөӣдёҖзӯүеҘ–еҗҺпјҢд»–зҰ»ејҖе…¬еҸёпјҢжҲҗдәҶдёҖеҗҚAppзӢ¬з«ӢејҖеҸ‘иҖ…вҖ”вҖ”дёҚе°‘з”ЁжҲ·зҺ©иҝҮзҡ„гҖҠзӮјйҮ‘жңҜеёҲгҖӢеҸҠз”ЁиҝҮзҡ„иҫ“е…Ҙжі•DinoгҖҒMoniCon зӯү AppпјҢйғҪеҮәиҮӘд»–е’Ңеӣўйҳҹд№ӢжүӢгҖӮ
гҖҖгҖҖдёҚзҹҘжҳҜдёҚжҳҜеӨ©з”ҹдҪҝ然пјҢвҖңеҲӣйҖ дёҚеҜ»еёёзҡ„дёңиҘҝвҖқиҝҷдёҖзҗҶеҝөиҙҜз©ҝдәҶжқҺжҳҹдҪ‘зҡ„жҲҗй•ҝиҪЁиҝ№гҖӮе…ӯе№ҙзә§зҡ„ж—¶еҖҷд»–и§үеҫ— iOS еә”з”ЁеҘҪй…·пјҢйӮЈж®өеңЁеұҸ幕дёҠж“ҚжҺ§зү©дҪ“移еҠЁзҡ„д»Јз ҒпјҢжҲҗдёәд»–жҺўзҙўж•°еӯ—дё–з•Ңзҡ„иө·зӮ№пјҢд№ҹдҝғдҪҝд»–ејҖеҸ‘еҮәдёҖж¬ҫеҹәдәҺйҮҚеҠӣж„ҹеә”зҡ„е°ҸжёёжҲҸпјҢе°қеҲ°еҲӣйҖ зҡ„д№җи¶ЈгҖӮ
гҖҖгҖҖеҪ“дёҡз•ҢиҝҳеңЁи®Ёи®әиҷҡжӢҹзҺ°е®һзҡ„еҸҜиЎҢжҖ§ж—¶пјҢд»–зҡ„зӣ®е…үе·ІжҠ•еҗ‘жӣҙеүҚжІҝзҡ„вҖңз©әй—ҙи®Ўз®—вҖқпјҢ并еӮ¬з”ҹдәҶиҷҡжӢҹеҢ–еӯҰе®һйӘҢе®ӨAppгҖҠзӮјйҮ‘жңҜеёҲгҖӢгҖӮд»–д»Һи®ҫеӨҮзҡ„зңҹе®һжёІжҹ“иғҪеҠӣдёӯиҺ·еҫ—зҒөж„ҹпјҢиҗҢз”ҹдәҶе°Ҷе®Ңж•ҙе®һйӘҢе®ӨвҖңжҗ¬иҝӣвҖқз”ЁжҲ·еҚ§е®Өзҡ„еӨ§иғҶжғіжі•вҖ”вҖ”йҖҡиҝҮж‘Ҷж”ҫиҷҡжӢҹзҡ„зғ§жқҜдёҺиҜ•еүӮпјҢи®©дҪҝз”ЁиҖ…иғҪдәІжүӢж··еҗҲ并и§ӮеҜҹжІёи…ҫгҖҒзӮёиЈӮжҲ–еҸҳиүІзӯүеҢ–еӯҰеҸҚеә”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д»–дёҺжӣҫз»Ҹзҡ„еӨ§еӯҰе®ӨеҸӢе…ұеҗҢе°ҶиҝҷдёҖжһ„жғіеҸҳдёәзҺ°е®һпјҢеңЁз”ЁжҲ·зңјеүҚе‘ҲзҺ°еҮәдёҖеј зңҹе®һзҡ„е®һйӘҢжЎҢпјҢи®©йӮЈдәӣйҖҡеёёйңҖиҰҒжҳӮиҙөи®ҫеӨҮе’Ңзү№е®ҡеңәжүҖзҡ„еӨҚжқӮеҢ–еӯҰе®һйӘҢпјҢеҸҳеҫ—и§ҰжүӢеҸҜеҸҠгҖӮиҝҷдёӘйЎ№зӣ®дёҚд»…иҺ·еҫ—дәҶ2024е№ҙдёӯеӣҪй«ҳж Ўи®Ўз®—жңәеӨ§иөӣ移еҠЁеә”з”ЁеҲӣж–°иөӣеҗҜиҲӘиөӣйҒ“зҡ„дёҖзӯүеҘ–пјҢжӣҙи®©д»–зҷ»дёҠдәҶWWDCпјҲиӢ№жһңе…ЁзҗғејҖеҸ‘иҖ…еӨ§дјҡпјүзҡ„иҲһеҸ°пјҢ并дёҺиӢ№жһңе…¬еҸёCEOи’Ӯе§ҶВ·еә“е…Ӣи§ҒйқўпјҢе®ҢжҲҗдәҶдёҖж¬Ўд»Һе…ҙи¶ЈеҲ°дё“дёҡзҡ„й—ӯзҺҜгҖӮ
гҖҖгҖҖд№ҹжӯЈжҳҜеңЁеӨ§еҺӮд»»иҒҢжңҹй—ҙпјҢжқҺжҳҹдҪ‘жҢҒз»ӯжҺўзҙўдёӘдәәйЎ№зӣ®зҡ„еҸҜиғҪжҖ§гҖӮеҪ“иӢ№жһңVision ProпјҲдёҖж¬ҫ AR дёҺ VR иһҚеҗҲзҡ„ж··еҗҲзҺ°е®һи®ҫеӨҮпјүеҸ‘еёғеҲқжңҹд»…ж”ҜжҢҒиӢұж–Үиҫ“е…Ҙж—¶пјҢд»–ејҖеҸ‘зҡ„иҫ“е…Ҙжі•DinoйҖҡиҝҮвҖңз©әй—ҙе°ҸзӘ—+иҜӯйҹіиҫ“е…ҘвҖқзҡ„еҲӣж–°з»„еҗҲпјҢжҲҗдёәVisionOSпјҲVision Proзі»з»ҹпјүдёҠйҰ–ж¬ҫдёӯж–Үиҫ“е…Ҙжі•пјҢиҝ…йҖҹзҷ»дёҠд»ҳиҙ№жҰңеүҚеҚҒгҖӮиҖҢи®© iPad иҝһжҺҘ SwitchгҖҒзӣёжңәзҡ„еә”з”Ё MoniConпјҢеҸҜдҪҝ iPad ж‘Үиә«еҸҳдёәжёёжҲҸдё»жңәдёҺзӣёжңәзҡ„дҫҝжҗәжҳҫзӨәеұҸпјҢйҖҡиҝҮзІҫеҮҶзҡ„жҠҖжңҜе®һзҺ°е’Ңз”ЁжҲ·дҪ“йӘҢдјҳеҢ–пјҢ收иҺ·дәҶ13дёҮз”ЁжҲ·зҡ„и®ӨеҸҜгҖӮ
гҖҖгҖҖд»Ҡе№ҙд»–з»ҲдәҺдёӢе®ҡеҶіеҝғзҰ»ејҖеӨ§еҺӮпјҢиў«й—®еҸҠиҝҷд»ҪйҖүжӢ©зҡ„еә•ж°”жқҘжәҗпјҢжқҺжҳҹдҪ‘зҡ„зӯ”жЎҲе§Ӣз»ҲжҳҺзЎ®пјҡжҳҜзғӯзҲұгҖӮеҜ№д»–жқҘиҜҙпјҢзғӯзҲұзҡ„д»·еҖјдёҚеңЁдәҺдёҮе…ЁеҮҶеӨҮеҗҺзҡ„е®ҢзҫҺе‘ҲзҺ°пјҢиҖҢеңЁдәҺе…ҲиЎҢеҠЁгҖӮ
гҖҖгҖҖд»–иҜҙпјҢеҪ“дёҖдёӘзӮ№еӯҗеҮәзҺ°пјҢз«ӢеҚіжҠ•е…ҘдёӨе°Ҹж—¶еҒҡеҮәжңҖзІ—зіҷзҡ„жј”зӨәзүҲпјҢе“ӘжҖ•жІЎжңүз•ҢйқўпјҢеҸӘиҰҒиғҪдј иҫҫж ёеҝғжҰӮеҝөе°ұеӨҹдәҶгҖӮеёҰзқҖиҝҷдёӘеҺҹе§ӢзүҲжң¬еҺ»ж”¶йӣҶиә«иҫ№дәәжңҖзӣҙжҺҘзҡ„еҸҚйҰҲвҖ”вҖ”ж— и®әжҳҜвҖңиҝҷжІЎз”ЁвҖқзҡ„еҗҰе®ҡпјҢиҝҳжҳҜвҖңеҰӮжһңеҠ дёҠжҹҗдёӘеҠҹиғҪдјҡжӣҙеҘҪвҖқзҡ„е»әи®®пјҢйғҪжҲҗдёәдёӢдёҖжӯҘиЎҢеҠЁзҡ„зІҫеҮҶеҜјиҲӘгҖӮжҺҘзқҖпјҢд»–з”ЁдёӨеӨ©ж—¶й—ҙеҝ«йҖҹж•ҙеҗҲиҝҷдәӣе»әи®®пјҢеҒҡеҮәе…·еӨҮеҹәжң¬дҪҝз”ЁжөҒзЁӢзҡ„жөӢиҜ•зүҲпјҢеҸ‘еёғеҲ°зӨҫеҢәе’Ңе°ҸиҢғеӣҙзӨҫдәӨе№іеҸ°дёҠгҖӮеҪ“еҮ зҷҫдёӘзңҹе®һз”ЁжҲ·зҡ„еҸҚйҰҲж¶Ңе…ҘпјҢд»–еҶҚиҠұдёӨе‘ЁзІҫеҝғжү“зЈЁпјҢжҺЁеҮәжңҖе°ҸеҸҜиЎҢдә§е“Ғ并жһңж–ӯдёҠжһ¶гҖӮд»–иҜҙпјҢвҖңиҙҙиҝ‘з”ЁжҲ·йңҖжұӮзҡ„дә§е“ҒпјҢдёҖе®ҡдјҡиў«йңҖиҰҒ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йҖҡиҝҮеҝ«йҖҹйӘҢиҜҒгҖҒе°ҸжӯҘиҝӯд»Јзҡ„иҠӮеҘҸпјҢд»–еҮ д№ҺдёӨе‘Ёе°ұејҖеҸ‘дёҖж¬ҫAppгҖӮжңүдәӣдә§е“ҒжҲ–и®ёзјәд№Ҹй•ҝжңҹд»·еҖјпјҢдҪҶ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зЎ®дҝқдәҶд»–дёҺз”ЁжҲ·йңҖжұӮзҡ„зҙ§еҜҶиҝһжҺҘпјҢи®©еҲӣйҖ еҠӣе§Ӣз»ҲдҝқжҢҒеңЁжҙ»и·ғзҠ¶жҖҒгҖӮйҷӨжӯӨд№ӢеӨ–пјҢд»–и®ӨеҗҢд№”еёғж–ҜвҖңиҝһзӮ№жҲҗзәҝвҖқзҡ„зҗҶеҝөпјҢ并解йҮҠйҒ“пјҡдҪ дёҚзҹҘйҒ“жңӘжқҘ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йҖүдҪ зғӯзҲұ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и®Өзңҹең°еҒҡеҘҪе®ғпјҢ并且衷еҝғең°жңҹжңӣжңӘжқҘдјҡеҫ—еҲ°дёҖдёӘеҘҪ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
гҖҖгҖҖзҰ»ејҖеӨ§еҺӮзҡ„еҶіе®ҡпјҢд№ҹ并йқһдёҖж—¶еҶІеҠЁгҖӮзЁіе®ҡзҡ„и–Әж°ҙгҖҒжҲҗзҶҹзҡ„жҷӢеҚҮйҖҡйҒ“гҖҒе№іеҸ°иө„жәҗзҡ„ж”ҜжҢҒвҖ”вҖ”иҝҷдәӣ他并йқһдёҚдәҶи§ЈгҖӮд»–д№ҹзҹҘйҒ“пјҢзӢ¬з«ӢејҖеҸ‘ж„Ҹе‘ізқҖиҰҒзӢ¬иҮӘйқўеҜ№дә§е“Ғе®ҡдҪҚгҖҒжҠҖжңҜе®һзҺ°гҖҒеёӮеңәжҺЁе№ҝзҡ„е…Ёй“ҫжқЎжҢ‘жҲҳпјҢд»»дҪ•дёҖдёӘзҺҜиҠӮзҡ„еӨұиҜҜйғҪеҸҜиғҪеҜјиҮҙж•°жңҲеҝғиЎҖд»ҳиҜёдёңжөҒгҖӮ
гҖҖгҖҖдҪҶй«ҳйЈҺйҷ©дјҙйҡҸзқҖвҖңй«ҳд№җи¶ЈвҖқгҖӮд»–иҜҙпјҢвҖңзӢ¬з«ӢејҖеҸ‘иҷҪ然иҰҒжүҝжӢ…жӣҙеӨҡйЈҺйҷ©е’ҢжҲҗжң¬пјҢдҪҶеҪ“з”ЁжҲ·еҸ‘зҺ°дҪ зІҫеҝғи®ҫи®Ўзҡ„жҹҗдёӘеҠҹиғҪзңҹжӯЈи§ЈеҶідәҶжҹҗдёӘй—®йўҳпјҢйӮЈз§ҚжҲҗе°ұж„ҹжҳҜж— еҸҜжӣҝд»Јзҡ„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°Ҫз®Ўиә«иҫ№дёҚд№ҸиҙЁз–‘зҡ„еЈ°йҹіпјҢжқҺжҳҹдҪ‘еҚҙе§Ӣз»ҲдҝқжҢҒзқҖжё…йҶ’зҡ„и®ӨзҹҘгҖӮд»–зҹҘйҒ“иҮӘе·ұиғҪеӨҹе°Ҷжғіжі•иҪ¬еҢ–дёәзҺ°е®һпјҢд№ҹжҳҺзҷҪеңЁдҪ•з§ҚеӨҚжқӮзЁӢеәҰзҡ„й—®йўҳдёҠйңҖиҰҒеҜ»жұӮеҗҲдҪңгҖӮиҝҷз§ҚеҜ№иҮӘиә«иҫ№з•ҢдёҺиғҪеҠӣзҡ„жҠҠжҸЎпјҢи®©д»–иғҪеӨҹдёәжҜҸдёҖдёӘйҖүжӢ©иҙҹиҙЈгҖӮ
гҖҖгҖҖж— дәәжңәзј–йҳҹеёҲ
гҖҖгҖҖвҖңжҲ‘зҡ„иҲһеҸ°жҳҜж•ҙдёӘеӨңз©ә вҖқ
гҖҖгҖҖвҖңе“ҮпјҢиҝҷд№ҹеӨӘеҘҪзңӢдәҶеҗ§пјҒвҖқжҜҸеҪ“еӨңз©әиў«ж•°зҷҫжһ¶ж— дәәжңәзӮ№дә®пјҢжҜҸеҪ“еҗ¬еҲ°и§Ӯдј—еҸ‘еҮәзҡ„дёҖеЈ°еЈ°жғҠеҸ№пјҢ26еІҒзҡ„еҲҳдҪіжҳ•зҹҘйҒ“пјҢиҮӘе·ұдёүе№ҙеүҚйӮЈдёӘвҖңдёҚжҢүеёёзҗҶеҮәзүҢвҖқзҡ„иҒҢдёҡйҖүжӢ©пјҢеҒҡеҜ№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д»ҺжӯҰжұүдҪ“иӮІеӯҰйҷўдҪ“иӮІз»ҸжөҺз®ЎзҗҶдё“дёҡжҜ•дёҡеҗҺпјҢеҘ№жІЎжңүеғҸеҗҢеӯҰ们йӮЈж ·иҝӣе…ҘдҪ“иӮІиЎҢдёҡпјҢиҖҢжҳҜжҠ•иә«дёҖдёӘеҪ“ж—¶иҝҳжһҒдёәе°Ҹдј—зҡ„йўҶеҹҹвҖ”вҖ”ж— дәәжңәзј–йҳҹеёҲгҖӮеҰӮд»ҠпјҢеҘ№е·ІжҳҜе…¬еҸёзҡ„вҖңдёҡеҠЎиҖҒжүӢвҖқпјҢеңЁе№•еҗҺз»ҹзӯ№зқҖдёҖеңәеңәз»ҡдёҪзҡ„вҖңеӨ©з©әз§Җ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вҖңд№ӢеүҚд№ҹжІЎжғіиҝҮдјҡеҒҡиҝҷдёҖиЎҢпјҢжҜ•дёҡж—¶зңӢеҲ°жӢӣиҒҳпјҢи§үеҫ—ж— дәәжңәиЎЁжј”еҫҲжңүж„ҸжҖқпјҢе°ұжҠ•дәҶз®ҖеҺҶгҖӮвҖқеҲҳдҪіжҳ•иҜҙпјҢе°Ҫз®Ўдё“дёҡдёҚеҜ№еҸЈпјҢиҮӘе·ұеҚҙеҮӯзқҖеҜ№жңӘзҹҘйўҶеҹҹзҡ„еҘҪеҘҮеҝғдёҺеӯҰд№ иғҪеҠӣпјҢжҲҗеҠҹи·ЁиЎҢе…ҘиҒҢгҖӮ
гҖҖгҖҖд»ӨеҘ№и®°еҝҶжңҖж·ұеҲ»зҡ„дёҖж¬Ўе·ҘдҪңз»ҸеҺҶпјҢжҳҜе’ҢеӣўйҳҹеңЁиҘҝи—Ҹжө·жӢ”3700зұізҡ„й«ҳеҺҹдёҠе…ӢжңҚй«ҳеҺҹеҸҚеә”гҖҒжҒ¶еҠЈеӨ©ж°”гҖҒдҝЎеҸ·е№Іжү°зӯүйҮҚйҮҚеӣ°йҡҫпјҢжҲҗеҠҹе®ҢжҲҗдәҶеҪ“ең°йҰ–еңәж— дәәжңәиЎЁжј”гҖӮеҪ“ж— дәәжңәзј–йҳҹжңҖз»ҲеңЁеӨңз©әдёӯе®ҢзҫҺе‘ҲзҺ°ж—¶пјҢжүҖжңүиү°иҫӣйғҪеҢ–дёәдәҶе·ЁеӨ§зҡ„жҲҗе°ұж„ҹгҖӮ
гҖҖгҖҖеңЁдҪҺз©әз»ҸжөҺзӣёе…іж”ҝзӯ–зҡ„жңүеҠӣж”ҜжҢҒдёӢпјҢж— дәәжңәиЎҢдёҡд№ҹеңЁи“¬еӢғеҸ‘еұ•гҖӮвҖңеҲҡе…ҘиЎҢж—¶пјҢеӨ§е®¶еҗ¬еҲ°жҲ‘зҡ„иҒҢдёҡйғҪдјҡдёҖи„ёиҢ«з„¶гҖӮзҺ°еңЁ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дәәдәҶ解并и®ӨеҸҜиҝҷдёӘиЎҢдёҡгҖӮвҖқеҲҳдҪіжҳ•ж•Ҹй”җең°еҜҹи§үеҲ°дәҶиҒҢдёҡзӨҫдјҡи®ӨеҸҜеәҰзҡ„еҸҳеҢ–гҖӮвҖңжҲ‘жӣҙеғҸжҳҜдёҖдёӘвҖҳеҜјжј”вҖҷ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жҲ‘зҡ„иҲһеҸ°жҳҜеӨңз©әпјҢжј”е‘ҳжҳҜж— дәәжңәгҖӮвҖқеҲҳдҪіжҳ•иҝҷж ·еҪўе®№иҮӘе·ұ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
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ж— дәәжңәиЎЁжј”е…¬еҸёвҖңй•ҝжұҹеҚғжңәвҖқзҡ„дёҖеҗҚж— дәәжңәзҫӨйЈһиЎҢ规еҲ’е‘ҳпјҢеҘ№зҡ„е·ҘдҪңиҝңдёҚжӯўвҖңйЈһж— дәәжңәвҖқйӮЈд№Ҳз®ҖеҚ•пјҢиҖҢжҳҜиҰҒиҙҹиҙЈз»ҹзӯ№ж•ҙеңәж— дәәжңәиЎЁжј”д»ҺеҲӣж„ҸеҲ°иҗҪең°зҡ„е…ЁиҝҮзЁӢгҖӮеҘ№еёҰйўҶдёҖдёӘ5дәәе·ҰеҸізҡ„е°ҸеӣўйҳҹпјҢиҙҹиҙЈеҜ№жҺҘе®ўжҲ·йңҖжұӮгҖҒи®ҫи®ЎиЎЁжј”з”»йқўгҖҒзј–зЁӢи°ғиҜ•гҖҒзҺ°еңәжү§иЎҢпјҢжҜҸдёҖдёӘзҺҜиҠӮйғҪйңҖзІҫеҮҶжҠҠжҺ§гҖӮ
гҖҖгҖҖвҖңиҷҪ然жҲ‘们дёҖзӣҙеңЁе№•еҗҺпјҢдҪҶжҜҸж¬ЎиЎЁжј”з»“жқҹпјҢеҗ¬еҲ°и§Ӯдј—зҡ„жғҠеҸ№пјҢе°ұи§үеҫ—дёҖеҲҮйғҪеҖјеҫ—гҖӮвҖқеңЁеҲҳдҪіжҳ•зңӢжқҘпјҢиҝҷз§ҚеҚіж—¶зҡ„еҸҚйҰҲе’ҢејәзғҲзҡ„жҲҗе°ұж„ҹпјҢжҳҜеҲ«зҡ„е·ҘдҪңйҡҫд»ҘжҸҗдҫӣзҡ„гҖӮ
гҖҖгҖҖйҷӨдәҶзӢ¬зү№зҡ„е·ҘдҪңдҪ“йӘҢпјҢеҲҳдҪіжҳ•зҡ„е·ҘдҪңзҠ¶жҖҒд№ҹжү“з ҙдәҶжңқд№қжҷҡдә”зҡ„еӣәе®ҡжЁЎејҸгҖӮвҖңиҷҪ然дёҚз”ЁжҜҸеӨ©йғҪеҺ»е…¬еҸёжү“еҚЎдёҠзҸӯпјҢдҪҶжңүж—¶е®ўжҲ·еҸҚйҰҲдёҖжқҘпјҢе°ұз®—жҳҜжҷҡдёҠ12зӮ№жҲ‘们д№ҹдјҡеҠ зҸӯдҝ®ж”№гҖӮвҖқеҘ№иҜҙпјҢвҖңжҲ‘дёҚи§үеҫ—иҝҷжҳҜиҙҹжӢ…пјҢеӣ дёәжҲ‘еңЁеҒҡиҮӘе·ұзңҹжӯЈ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дәӢжғ…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ҲҳдҪіжҳ•е‘ҠиҜүеҢ—йқ’жҠҘи®°иҖ…пјҢеҘ№зҡ„еӣўйҳҹдёӯпјҢ90еҗҺе’Ң00еҗҺжҲҗдәҶвҖңеӨ§йғЁйҳҹвҖқгҖӮвҖңиҝҷдёӘиЎҢдёҡе°ұеғҸвҖҳе…ЁиғҪзү№з§Қе…өвҖҷпјҢд»Җд№ҲйғҪиҰҒжҮӮдёҖзӮ№пјҢеҸҲиҰҒжңүеҫҲејәзҡ„жҠ—еҺӢиғҪеҠӣ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Ҙ№и®ӨдёәпјҢж–°е…ҙиЎҢдёҡжңҖйңҖиҰҒзҡ„жҳҜеӨҚеҗҲеһӢдәәжүҚвҖ”вҖ”ж—ўиҰҒжҮӮжҠҖжңҜпјҢеҸҲиҰҒжҮӮз®ЎзҗҶпјӣж—ўиҰҒжңүеҲӣж„ҸпјҢеҸҲиҰҒжһҒе…¶дёҘи°ЁгҖӮ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ж–°е…ҙиЎҢдёҡйҮҢпјҢдё“дёҡиғҢжҷҜеӣә然йҮҚиҰҒпјҢдҪҶжҢҒз»ӯеӯҰд№ зҡ„иғҪеҠӣе’Ңзғӯжғ…жүҚжҳҜзңҹжӯЈзҡ„вҖңзЎ¬йҖҡиҙ§вҖқгҖӮеӨ§еӯҰж•ҷиӮІиөӢдәҲеҘ№зҡ„дёҚжҳҜжҹҗдёӘе…·дҪ“жҠҖиғҪпјҢиҖҢжҳҜзі»з»ҹжҖқз»ҙе’ҢеҚҸи°ғиғҪеҠӣпјҢжӯЈжҳҜиҝҷдәӣвҖңеҸҜиҝҒ移иғҪеҠӣвҖқи®©еҘ№еңЁж–°йўҶеҹҹеҗҢж ·жёёеҲғжңүдҪҷгҖӮ
гҖҖгҖҖеҜ№дәҺеҚіе°Ҷиҝӣе…ҘиҒҢеңә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пјҢеҘ№зҡ„е»әи®®жҳҜпјҡвҖңжҲ‘们жӢ©дёҡж—¶еә”иҜҘжҠҠзғӯзҲұе’Ңе…ҙи¶Јзҡ„дјҳе…Ҳзә§еҫҖеүҚжҺ’дёҖжҺ’гҖӮе°ұеғҸ家дәәзҹҘйҒ“жҲ‘иҰҒеҺ»еҒҡж— дәәжңәзӣёе…іе·ҘдҪңзҡ„ж—¶еҖҷеҜ№жҲ‘иҜҙзҡ„пјҡвҖҳ既然дҪ йҖүжӢ©дәҶпјҢд№ҹеҫҲж„ҹе…ҙи¶ЈпјҢйӮЈе°ұеҺ»еҒҡеҗ§пјҒвҖҷвҖқ
гҖҖгҖҖAIз®—жі•з ”з©¶е‘ҳ
гҖҖгҖҖеё®еҢ»з”ҹйҖ вҖңйҖҸжҳҺеҝғи„ҸвҖқ
гҖҖгҖҖдёҖйў—и·іеҠЁзҡ„еҝғи„ҸпјҢеҰӮдҪ•еҸҳеҫ—вҖңйҖҸжҳҺвҖқпјҢи®©еҢ»з”ҹдёҖзңјзңӢжё…жҜҸдёҖеӨ„з»“жһ„дёҺз–Өз—•пјҹиҝҷеҗ¬иө·жқҘеғҸжҳҜ科幻з”өеҪұдёӯзҡ„еңәжҷҜпјҢеҚҙжҳҜ95еҗҺз ”з©¶е‘ҳиӢҸеӯҗиҙӨжҜҸеӨ©йғҪеңЁжҺЁиҝӣ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д»Ҡе№ҙеҲҡд»ҺеҲ©зү©жөҰеӨ§еӯҰеҚҡеЈ«жҜ•дёҡзҡ„еҘ№пјҢжІЎжңүз•ҷеңЁжө·еӨ–пјҢиҖҢжҳҜеҠ е…Ҙжҷәжәҗз ”з©¶йҷўз”ҹе‘ҪжЁЎжӢҹз ”з©¶дёӯеҝғпјҲд»ҘдёӢз®Җз§°вҖңжҷәжәҗвҖқпјүпјҢеңЁеј жҒ’иҙөж•ҷжҺҲзҡ„жҢҮеҜјдёӢпјҢдё»еҜјвҖңйҖҸжҳҺеҝғи„ҸвҖқвҖ”вҖ”дёҖеҘ—е…ЁиҮӘеҠЁеҝғи„Ҹ3Dз–Өз—•йҮҚе»әдёҺе®ҡйҮҸеҲҶжһҗзі»з»ҹзҡ„йЎ№зӣ®гҖӮдёәдәҶжүҫеҲ°дёҖдёӘиғҪйҡҸж—¶и§ӮеҜҹгҖҒе»әжЁЎзҡ„еҝғи„ҸпјҢеҘ№е°ұз”ЁиҮӘе·ұзҡ„еҝғи„ҸпјҢжү«жҸҸи§ӮеҜҹпјҢеҒҡжЁЎеһӢжЁЎжӢҹгҖӮиҖҢеҘ№зҡ„з»ҸеҺҶпјҢд№ҹжҳҜж–°е…ҙиҒҢдёҡвҖ”вҖ”AIз®—жі•з ”з©¶е‘ҳ们зҡ„дёҖдёӘзј©еҪұгҖӮ
гҖҖгҖҖй«ҳдёӯж—¶пјҢиӢҸеӯҗиҙӨе°ұжӣҫжғіиҝҮеӯҰеҢ»гҖӮеҘ№еқҰиЁҖпјҢвҖңдәәжңҖеә”иҜҘе…іеҝғзҡ„пјҢе°ұжҳҜиә«дҪ“зҡ„еҒҘеә·гҖӮвҖқдҪҶеӣ зјҳйҷ…дјҡиө°дёҠдәҶи®Ўз®—жңә科еӯҰзҡ„йҒ“и·ҜгҖӮ
гҖҖгҖҖжӯЈеӣ еҰӮжӯӨпјҢеҚҡеЈ«жҜ•дёҡеҗҺпјҢеҘ№йҖүжӢ©е°ҶдёӨиҖ…з»“еҗҲпјҢеқҡе®ҡең°иө°еҗ‘дәҶвҖңAI for healthcareвҖқпјҲз”ҹзү©еҢ»з–—дәәе·ҘжҷәиғҪж–№еҗ‘пјүгҖӮеҘ№еӣһеҝҶйҒ“пјҢвҖңжҲ‘еҪ“ж—¶зҡ„жғіжі•жҳҜйҖүжӢ©еҒҸдәӨеҸүзҡ„ж–№еҗ‘пјҢеҲ©з”Ёд№ӢеүҚеӯҰд№ 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еҺ»и§ЈеҶідёҖдәӣдёҙеәҠдёҠ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жңҖз»ҲеҮҸиҪ»еҢ»з”ҹзҡ„иҙҹжӢ…пјҢжҸҗй«ҳж•ҙдҪ“еҢ»з–—ж°ҙе№і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иҝӣе…ҘжҷәжәҗеҗҺпјҢеҘ№еҸ‘зҺ°иҝҷйҮҢжӢҘжңүеғҸеӨ§еӯҰе®һйӘҢе®ӨдёҖж ·зҡ„еҲӣж–°ж°ӣеӣҙ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еҶ…йғЁзҡ„вҖңйҷўй•ҝдёӢеҚҲиҢ¶вҖқжҙ»еҠЁпјҢиҝҳжҳҜеҜ№еӨ–зҡ„жҷәжәҗеӨ§дјҡпјҢйғҪеңЁдёҚж–ӯжҝҖеҸ‘и·Ёз•ҢжҖқиҖғгҖӮеңЁиӢҸеӯҗиҙӨзңӢжқҘпјҢиҰҒе°ҶAIзҡ„жҪңеҠӣиҪ¬еҢ–дёәйҖӮз”ЁдәҺеҢ»з–—еңәжҷҜпјҢжңҖе…ій”®зҡ„ж ёеҝғз«һдәүеҠӣ并йқһжҳҜз®—жі•пјҢиҖҢжҳҜе·ҘзЁӢиғҪеҠӣвҖ”вҖ”еҚізі»з»ҹеҢ–гҖҒй«ҳиҙЁйҮҸең°е°ҶдёҖдёӘжғіжі•д»Һйӣ¶еҲ°дёҖе®һзҺ°иҗҪең°зҡ„иғҪеҠӣгҖӮ
гҖҖгҖҖеҘ№иҙҹиҙЈзҡ„йЎ№зӣ®жӯЈеңЁе®һи·өиҝҷдёҖзҗҶеҝөгҖӮеҹәдәҺзҺ°еңЁеҒҡзҡ„1.0зүҲжң¬пјҢеӣўйҳҹеҗҺз»ӯе°ҶйҖҗжӯҘиһҚе…Ҙд»ҝзңҹгҖҒеӨ§жЁЎеһӢеҜ№иҜқзӯүжӣҙеӨҡеҠҹиғҪпјҢзӣ®ж ҮжҳҜжңҖз»ҲиғҪиҫ…еҠ©еҢ»з”ҹе®ҢжҲҗж’°еҶҷжҠҘе‘ҠгҖҒе®һж–ҪиҷҡжӢҹжүӢжңҜзӯүеӨҚжқӮе·ҘдҪңгҖӮзӣ®еүҚпјҢжҗӯиҪҪеңЁз¬”и®°жң¬з”өи„‘дёҠзҡ„иҪҜ件еҚіе°Ҷиҝӣе…ҘдёҙеәҠжөӢиҜ•пјҢиҝҷжҳҜд»Һд»Јз Ғиө°еҗ‘з—…жҲҝзҡ„е…ій”®дёҖжӯҘгҖӮ
гҖҖгҖҖз§‘з ”д№Ӣи·Ҝ并йқһдёҖеёҶйЈҺйЎәгҖӮеңЁе®һйҷ…еә”з”ЁдёӯпјҢеҘ№йҒҮеҲ°дәҶи®ёеӨҡжЁЎеһӢд»Һе®һйӘҢе®Өиө°еҗ‘дёҙеәҠзҡ„е…ёеһӢжҢ‘жҲҳ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д»ҺдәҢз»ҙжЁЎеһӢеҚҮзә§еҲ°дёүз»ҙжЁЎеһӢж—¶пјҢзҺ°йңҖиҰҒеӨ§жү№йҮҸзҡ„ж•°жҚ®жүҚиғҪи®ӯз»ғеҮәдёҖдёӘжЁЎеһӢпјҢдёҖж—Ұзңҹе®һеә”з”ЁеңәжҷҜзҡ„ж•°жҚ®дёҺеҺҹе§Ӣи®ӯз»ғж•°жҚ®дёҚдёҖиҮҙпјҢжЁЎеһӢиЎЁзҺ°е°ұеӨ§жү“жҠҳжүЈгҖӮеҘ№дёҺеӣўйҳҹе°ұйңҖиҰҒдёҚж–ӯи°ғиҜ•пјҢи®©жЁЎеһӢеңЁзңҹе®һзҡ„еә”з”ЁеңәжҷҜдёӢд№ҹиғҪеҘҪз”ЁгҖӮ
гҖҖгҖҖеҸҰдёҖдёӘжҢ‘жҲҳжқҘиҮӘеҝғи„Ҹз–Өз—•зҡ„еҲҶеүІдёҺеҸҜи§ҶеҢ–гҖӮзӣ®еүҚAIжЁЎеһӢзҡ„зІҫеҮҶеәҰе°ҡдёҚиғҪе®Ңе…Ёж»Ўи¶іеҢ»з”ҹиҰҒжұӮгҖӮ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йңҖиҰҒиҖҗеҝғпјҢжӣҙйңҖиҰҒдёҖз§ҚвҖңеӨҡдёҫдёҖеҸҚдёүпјҢеӨҡе°қиҜ•вҖқзҡ„жҖқз»ҙгҖӮ
гҖҖгҖҖеҘ№еҪўе®№иҝҷжҳҜдёҖз§ҚвҖңжңүзӣ®зҡ„жҖ§зҡ„еӨҡиҜ•вҖқпјҢжҜҸдёҖжӯҘйғҪжңүзӣёеҜ№жҳҺзЎ®зҡ„еҸҜиЎҢжҖ§еҲӨж–ӯпјҢзӣ®ж ҮжҳҜе°Ҷе·Іжңүзҡ„жҠҖжңҜиҝӣиЎҢжңүж•Ҳж•ҙеҗҲдёҺеҫ®и°ғпјҢжңҖз»Ҳи§ЈеҶідёҙеәҠдёӯзҡ„е…·дҪ“й—®йўҳгҖӮиҝҷз§Қд»ҺвҖңеҸ‘и®әж–ҮвҖқеҲ°вҖңйҖ иҪҜ件вҖқзҡ„жҖқз»ҙиҪ¬еҸҳпјҢи®©еҘ№жӣҙж·ұеҲ»ең°зҗҶи§ЈдәҶз§‘з ”зҡ„д»·еҖјеңЁдәҺи§ЈеҶіе®һйҷ…й—®йўҳгҖӮ
гҖҖгҖҖВ·и®°иҖ…жүӢи®°В·
гҖҖгҖҖжңүжғіжі•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йҮҚж–°е®ҡд№үвҖңеҘҪе·ҘдҪңвҖқ
гҖҖгҖҖеңЁз§‘еҲӣжөӘжҪ®еёӯеҚ·еҗ„иЎҢеҗ„дёҡзҡ„д»ҠеӨ©пјҢе№ҙиҪ»дәәзҡ„иҒҢдёҡйҖүжӢ©жӯЈеңЁжӮ„然еҸ‘з”ҹеҸҳеҢ–вҖ”вҖ”иҝӣе…Ҙдј з»ҹиЎҢдёҡе·ҘдҪңпјҢжҲ–иҖ…еҫ…еңЁеӨ§еҺӮзЁіе®ҡжҷӢеҚҮпјҢд№ҹи®ёжҳҜеҫҲеӨҡдәәзңјдёӯзҡ„вҖңе…үйІңдә®дёҪвҖқпјҢ然иҖҢ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дёҚеҶҚз•ҷжҒӢиҝҷж ·зҡ„е…үзҺҜпјҢиҖҢжҳҜйҖүжӢ©дёҖжқЎжӣҙеҠ иҮӘдё»зҡ„иҒҢдёҡйҒ“и·ҜпјҢеҘ”иөҙиҮӘе·ұзҡ„зғӯзҲұгҖӮ
гҖҖгҖҖжҜ”еҰӮзӢ¬з«ӢAppејҖеҸ‘иҖ…жқҺжҳҹдҪ‘йҖҡиҝҮиҮӘе·ұиҝ‘д№ҺеҒҸжү§зҡ„еёӮеңәж•Ҹж„ҹеәҰпјҢеҺ»жҚ•жҚүз”ЁжҲ·йңҖжұӮпјҢ然еҗҺйҖҡиҝҮжңҖе°ҸеҢ–жҲҗжң¬еҝ«йҖҹйӘҢиҜҒжғіжі•гҖӮд»–иҜҙиҮӘе·ұз§үжҢҒзқҖвҖңйҒ—жҶҫжңҖе°ҸеҢ–вҖқзҡ„еҺҹеҲҷпјҢе°ұжҳҜеҒҡйҖүжӢ©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дёҚз”ЁеҺ»иҖғиҷ‘收зӣҠжңҖеӨ§еҢ–пјҢвҖңеӣ дёәдҪ ж°ёиҝңдёҚзҹҘйҒ“е“ӘдёӘдёңиҘҝзҡ„收зӣҠжҳҜжңҖеӨ§зҡ„пјҢдҪҶжҳҜдҪ дёҖе®ҡиҰҒиҖғиҷ‘зҡ„жҳҜйҒ—жҶҫжңҖе°ҸеҢ–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иҖҢAIз®—жі•з ”з©¶е‘ҳиӢҸеӯҗиҙӨд№ҹйҖҗжёҗж„ҸиҜҶеҲ°пјҢеҘҪе·ҘдҪң并дёҚжҳҜвҖңеҗ¬иө·жқҘеҘҪеҗ¬вҖқпјҢиҖҢжҳҜиҰҒи§ЈеҶіе®һйҷ…й—®йўҳгҖӮ
гҖҖгҖҖиҝҷдәӣж–°е…ҙиҒҢдёҡеңЁз§‘еҲӣж—¶д»ЈеҸ‘еұ•зҡ„жөӘжҪ®дёӯжҳҫзӨәеҮәи¶ҠжқҘи¶ҠйҮҚиҰҒзҡ„д»·еҖјпјҢе№ҙиҪ»дәәд№ҹжүҫеҲ°дәҶејәзғҲзҡ„иҒҢдёҡи®ӨеҗҢж„ҹгҖӮеҜ№дәҺвҖңз”ҹжҲҗејҸдәәе·ҘжҷәиғҪеҠЁз”»еҲ¶дҪңе‘ҳвҖқиҝҷдёҖдәәзӨҫйғЁи®ӨиҜҒзҡ„ж–°иҒҢдёҡпјҢеҗҙз‘•иЎЁзӨәпјҡвҖңжҠҖжңҜдјҡеҝ«йҖҹиҝӯд»ЈпјҢе·Ҙе…·д№ҹеңЁдёҚж–ӯиҝӣеҢ–гҖӮеҜ№дәҺжҲ‘们иҝҷж ·жңүжғіжі•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иҖҢиЁҖпјҢиҝҷжӯЈжҳҜжңҖеҘҪзҡ„ж—¶д»ЈгҖӮвҖқиҖҢжҜҸеҪ“еӨң幕йҷҚдёҙпјҢеҸҲдёҖеңәж— дәәжңәиЎЁжј”еҚіе°ҶејҖе§ӢгҖӮж— дәәжңәзј–йҳҹеёҲеҲҳдҪіжҳ•з«ҷеңЁеӨң幕иҝҷдёҖиҲһеҸ°дёӢпјҢи§Ӯдј—зҡ„дёҖеЈ°еЈ°жғҠеҸ№пјҢжҳҜеҜ№иЎЁжј”зҡ„иөһзҫҺпјҢеңЁеҘ№зңӢжқҘпјҢд№ҹжҳҜеҜ№иҮӘе·ұиҒҢдёҡзҡ„иӮҜе®ҡгҖӮ
гҖҖгҖҖеҪ“и®ёеӨҡеҗҢйҫ„дәәд»ҚеңЁдёәвҖңдё“дёҡдёҚеҜ№еҸЈвҖқвҖңиө°зӢ¬жңЁжЎҘвҖқвҖңе°ұдёҡйҡҫвҖқз„Ұиҷ‘ж—¶пјҢиҝҷдәӣе№ҙиҪ»дәәеӢҮж•ўең°иө°еҮәдј з»ҹе°ұдёҡиөӣйҒ“пјҢз”ЁвҖңеҸҰзұ»вҖқиҒҢдёҡд№ҰеҶҷзӢ¬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е°ұдёҡж•…дәӢгҖӮ他们用иЎҢеҠЁиҜҒжҳҺпјҡ科еҲӣж—¶д»ЈпјҢвҖңеҘҪе·ҘдҪңвҖқзҡ„е®ҡд№үеә”иҜҘй…Қеҫ—дёҠиҮӘе·ұзҡ„йҮҺеҝғгҖӮ
гҖҖгҖҖж–Ү/е®һд№ з”ҹ иөөж¶өиҗұ еҲҳзҶҷеӘӣ
гҖҖгҖҖжң¬жҠҘи®°иҖ… 温婧
гҖҖгҖҖдҫӣеӣҫ/еҸ—и®ҝиҖ… з»ҹзӯ№/дҪҷзҫҺиӢұ





 дә¬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 11010102004843еҸ·
дә¬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 11010102004843еҸ·